书瑞的女店一经开设, 没得两月间便声名远播了去,且还没费甚么劲儿,不似当初十里街上小客栈开业时, 各般寻宣扬的法子,自费力又费钱。
能得回容易,一来是已经有了一套小客栈的宣扬法,径直套过来用, 寻人找人不费事, 都是老合作人了,稍再使些钱便是。而宣扬时, 因女店新鲜,颇有些噱头,比之寻常的客栈要好吸引客人得多。
像是传统的客栈, 无非是从距离城中哪处近, 客栈规模大小这些为特点来做介绍吸引客人, 听得多了, 住客也没觉得稀罕,不一定会选这住处,而女店专门承接女子和哥儿为引, 是城中旁的客栈所不能有的特点, 图个新鲜都会去瞧上一眼。
而往往那些上门看稀罕的,在客栈里见了陈设,若不是极个别十分刁钻的人,大抵都会选择住下。
二一则, 城里的人晓得了有这么一间客栈后,茶余饭后的当做新鲜事来说,自发的谈资, 不需要刻意鼓动就人传人的传开了。
第三项宣扬是来过店里的住客给的,一应好的服侍,教在女店落过脚的住客印象十分深刻,回去时,自也会当做一桩妙事来谈,广而推荐。
崔芮的生意经也好,放在客栈里的胭脂香料好卖,后是小书话本、薄酒果酒也跟着卖了起来
为此,书瑞的女店开起来以后,当真还没怎愁过生意。
年底上,书瑞盘着账,得意与陆凌说:
“依着这生意架势,我瞧用不得一两年女店就能开分号。这年节上,每日女店里都满客,还有前来没得住的,没得法子,转还给引到了小客栈那头去。人家信赖,虽是没得女店住,听闻同是我支的店,亦愿意选择。”
说起这,书瑞就觉得很欢喜,女店确实给他在女子哥儿中树立了个不错的口碑。
陆凌倒是也认女店的生意好,这才开多久,来储物铺上存货的外乡小商户竟都听说了他们府城有这样的客栈,还问了真假。
在城里有了名头还不足为奇,倒是难为外头都晓得了这生意事。
不过生意好归好,陆凌还是劝说书瑞道:“你也别把所有心思都一股脑的放在了生意事上,一忙起来不管不顾的,要紧着些身子。”
“我晓得。”
书瑞道:“女店上两个伙计跑堂迎客,灶事又有三妹掌着,我也便是过去在堂上打打算盘,给住客办入住,与人唠嗑几句闲,推销一二店里的胭脂香料,旁的时候操心不得多少。
没得那样傻还似和小客栈初开时那般。”
陆凌要不是看着店里伙计都足,只怕又得日日跟在人身前盯着了。
说着,书瑞搓了搓胳膊,觉着有些冷飕飕的,探脑袋去看是不是陆凌进来没把门窗关好,却又见严丝合缝的,便问:“外头可是又落雪了?”
陆凌见他觉冷,把一只手炉放去他手心里,在人旁侧坐下:“一直都在落,倒是比昨晚里要小了许多,撒的是些雪粒子。”
他看炭盆子里还燃着红炭,并没灭下去,不知书瑞怎又冷了,今年这冬里,似乎人格外的怕冷些,倒也是怪雪一日连着一日的下,冰天雪地的,城里不便,城外也恼火。
听得城外地势更高些的乡里还有受了雪灾的,进城的商户都直摇脑袋说如此天气不好做生意。
陆爹前些时候还随着同知前去乡里探访过灾情,户房也做筹集款项救济,他们俩以各自铺子的名义也捐了些钱,城中布告处张着大红榜,上头嘉奖公示了捐款的商户士人的名单。
“不知是不是在屋里头坐着盘账,身子没得动弹,守着炭盆儿竟也还觉冷。”
书瑞说着,折身委屈巴巴的钻到了陆凌的怀里去,这人身上不知怎就那样好,总是暖和的。近来夜里头要不教他抱着生暖,他总觉厚厚的被褥盖着也不暖和。
“冬月里便是受冷教人不好受。”
陆凌将人护在怀里,道:“要不得我再给你添个炭盆儿进来。”
书瑞在陆凌身上轻轻蹭了蹭,道:“那怕是得多娇贵,一间屋子竟还放三个取暖的。便是外头大户人家也没得这待遇。”
“哪里来的三个,拢共就脚下那炭盆儿,多放一个也没得人说。”
书瑞抬手捏了陆凌的耳朵一下,眨了眨眼:“这里不还有一个麽。”
陆凌嘴角轻扬,亲了亲书瑞的脸:“那我今朝就不过去铺子那头了,都在屋里。”
“这怎成。”
书瑞见人顺杆子就爬了上来,他合上了账簿,道:“原本便要关铺子放年节了,这几日上还是站好岗。”
“咱俩一道儿去三间铺子上看一眼,今朝就不在铺子上忙活。”
陆凌就晓他放不下生意事,也只好应了一声。
在屋里又待了会儿,他才前去给书瑞取了厚实的斗篷来,与人系上,叫了人套车,一同坐着出了门。
外头积雪多,白茫茫的一片,只在白中又能见着红艳艳的灯笼,偶听着小童在巷子间跑动扎炮的声音,嘻嘻哈哈的,倒是一派年节氛围。
“大郎君,夫郎,先且留步,有封急信。”
书瑞正探着半个脑袋看外头的雪色,马车还没走到巷子外的主街上去,家里的长工便拿着一封信追了来。
“谁人的信?”
“甘县老家那头送过来的,说是快马加鞭才递了来。俺看急,夫郎还没走远,就先拿了来。”
书瑞疑道:“老家那头,可是爹和娘或者二郎的信?”
“说是给夫郎您的。”
书瑞闻言将信接下,快是拆开了来瞧,陆凌也凑了过去看。
老家那头能来信的,又交待要送在书瑞手上,无非就是白家。
这两年上书瑞和白家联络的不多,倒是逢年过节的白大郎会送封信来,都是些客套的寒暄。
信通读下来,书瑞眉头紧锁,心绪有些复杂。便说若是寻常的节日问安信,不至这样火急火燎的,果真是生了事。
这信上说他表哥白大郎教人诬告以公谋私给关了起来,眼见过年了,时下却还在牢里备受苦楚,一家子人心头都跟油煎似的,让书瑞看在过去的情谊上,务必去求陆爹帮忙,通通路子把他表哥给弄出来。
好是轻巧的话。
他瞧着信是蒋氏写的,一头极不情愿跟他联络,一头也应当实在是没得法子了,信中言辞虽有低头求人做事的口吻,却还是难改蒋氏对他颐指气使的习惯。
故此读起来颇为怪异。
“诬告,没行些触犯律法为非作歹的事情,人轻易能诬告得了他?”
书瑞早从陆凌那处听说了他表哥任职时利用职务之便行私等诸多烂事,即便是陆凌不说这些,他心里其实也能猜到表哥做官不得多清正。
当初吴家肯捐海量的银子来扶他做官,无非就是想官场上有自己的人好行生意事,他表哥受人好才任得官,即便他是个正直的人,不愿去做以公谋私的事,可如何又由得他肯或是不肯的。
常言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他那官又不是靠着自己的真本事得的,看似是自己做,其实却是为别人而当,哪里能全凭自己意愿而为。
再一则,他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弟弟嫁给个老商做续弦也要去得那么个前程,骨子里可见不是个甚么正直之辈。
走至今日,完全是情理之中。
成婚那年白家人过来送亲,他就听李妈妈说白家依附的王县丞要调职了。
新任了官员来,官署上少不得要换一回血,新官不尽吃官署旧人那一套,他表哥手脚不干净,怕是给嫉恨的人捏着做了文章趁此要将他弄下去。
早预料了白家不是长久之相,能扑腾个三年才倒,也算是他们命好了。
陆凌道:“可要与他们走走门路?”
书瑞将信纸塞回信封里去,语气淡淡的:
“都这时候了,却也还不肯坦白交待,一心觉着是人诬告了他们,真走门路把他捞出来,往后只怕更有恃无恐的敛财害民,这般岂不是为虎作伥。”
“说不得到时还惹身骚来。捞定是捞不得的。”
他细细想了一番,晚间,陆爹从官署下职回来,书瑞还是同他提了一嘴这件事,问询陆爹白大郎可会掉脑袋。
陆爹言若没得人命官司,当罪不至死。
不过往前为着他和陆凌婚事的事打听来看,白大郎一旦被揭发,官职势必不保,再看现在的情形,又有人存了心治他,少不得吃板子后流放。
几番周折打听,果然如陆爹预判的差不多,白大郎得遭判流放。
言是人得发配往岭南一带,书瑞虽不曾去过岭南,却也听说如今那片毒虫瘴气十分可怕,白大郎打小就生在靠海一带,这厢过去,只怕在路上就得没命。
书瑞这几年在潮汐府上,白家的事他已都渐是放下了。
虽论不得多少情谊,但于外,他终究是在白家长大的,此番白家落魄,他若当真半点不顾忌,少不得再落下个无情无义的名。
他费心疏通了一番门路,原本要发配至岭南的白大郎转至了崖州,虽也一样是疾苦地,可到底还是在沿海一片,没得路上就丢了性命。
算是保他半条命,全了当年白家收养的情分,再多的,书瑞也做不到了。
人各有命,当初他从白家出来,今夕的日子也全凭自己闯出来的,靠人不如靠己。
白家也该在逆境里好好审视自己一番了。
此后,白大郎遭了发配,吴家受牵连,生意上大遭折损,白家也免不得抄家,还要赔付罚银,否则一样得下牢。
一时间蒋氏只得变卖了家财田产来弥补,光耀几载,最后又搬回了乡下。
然则这三年的光耀纯然便是透支后头的安顺日子才换下的,为了缴纳罚款,乡下的宅子卖了,田地也都几乎卖尽。
手上教榨了个干不说,从前好歹还是私塾先生娘子,在乡里一带颇有名望,谁人见着都客客气气的,这朝再回去,沦得了个罪臣家眷的名头,日里遭受指指点点,活似真煎熬。
午夜梦回,也试想当初若是没有和吴家来往,虽不得个大富大贵,却也过着安生日子
了却了白家事,书瑞心中也开阔松愉了好些。
今年正月热闹,陆钰中了举,陆爹在府衙里也颇有前程,人来人往的席面儿多得很。
他们自走动他们的,书瑞跟陆凌也有不少能走动的熟识。
好也是在此几年了,自结下了些过年能上门拜访的朋友。
一个正月下来,书瑞觉自己好似都吃得胖了。
白日在外头因怕冷衣得厚实,浑不显,家来时在屋子里解了外衣,单着寝衣时,他看着就觉自己比从前圆润了些。
陆凌本还觉哥儿女子的便总是格外关切自己的身形,本要笑他说真嫌自个儿胖了,那早间就喊他起来跟自己一起打拳。
不想去抱他时,摸着人肚子上还真比之前肉多了些似的,捏着软乎乎的。
“长些肉也好,身子没那样单薄,不惧冷。”
书瑞哼哼了两声:“谁要与你一起清早的起来打拳,以为人人都似你一般浑身牛劲儿没处使不成。”
说罢,复也去摸陆凌的肚子,这人倒是一直都维持的多好,腰腹摸着总是结实的。
晚间睡着,他都习惯了要去摸两下。
陆凌教他细软的手摸的心痒,一把将人的手给捉着,道:“你要不肯打拳,做点别的也成。”
书瑞啾了人一眼,晓他心头打的甚么主意,若往前他说不得就迎合了,只这正月上天气也还冷,虽快是开春儿了,可天气跟年冬前没差多少。
他解了衣裳怕冷,陆凌历来弄得动作大,春秋上天气不冷不热时还好,太热了太冷了他都不大肯干那事。
再者,他也不知是不是天气冷的缘故,人便格外的爱睡些,瞧这钻进被窝里来,就生了困意。
便同陆凌道:“白日出门吃了席面儿,乏得很,改明儿再说罢。”
“这话听你说好些回了,下次敷衍人怕是也该换套说辞了。”
陆凌有些不大高兴,下巴放在了书瑞的颈窝处。
“糊弄人都这样不上心。”
书瑞脑袋懵懵的,问他:“真的假的?”
他也觉着这话耳熟,但是却又不记得自己竟跟陆凌说了有几回了。
陆凌轻哼了一声。
书瑞瞧人好是傲娇的模样,翻了个身去面对着陆凌,抿嘴坏笑了下,伸了手过去。
过了些时候,想是松手,却教人给握住了不许放,又是好半晌,手都见酸麻了才得松开。
他凝着眉头,揉了揉发软的胳膊,轻推了陆凌一下,心想当真如何都不得轻松。
二月里,这日天气放晴,书瑞陪着柳氏在宅子里头做春饼来吃。
取乡里送的新鲜荠菜来煎了鸡子,怪是鲜香,书瑞吃了半张饼,忽得胃里头一阵翻江倒海,连是捂着嘴跑去了一头。
“哎哟,这是怎的了!”
柳氏赶忙去给书瑞顺了顺背,喊了人端水来:“可是饼不干净吃得反胃了?”
书瑞漱了漱口,吃了点茶水,稍才好些,只再闻着饼的油香气,不觉香了,反是恶心。
他紧着眉头:“不知是不是昨儿贪凉吃了些冷果子,这才使得胃里不好。”
柳氏听胃不痛快,如临大敌,生怕书瑞走了陆钰的老路,连就喊着要请大夫。
书瑞觉没得这样严重,但怕柳氏忧心,还是乖顺的说看一回诊,便喊了长工出去请。
陆凌打铺子那头回来,刚进巷子,就见着自家的长工引个背着医箱的大夫往宅子去,眉心一紧,连快步赶了去。
“家里谁不痛快?”
长工见陆凌急问,连道:“是夫郎,夫人教请个郎中瞧瞧。”
陆凌听得书瑞身子不适,更是快了步子进院儿去。
“你甭上火,只是将才吃饼有些犯恶心,没得甚么大症。”
书瑞见着板了一张脸回来的人,连安抚他,谁想看个大夫又给他恰撞着。
陆凌没言语,独是盯着给书瑞诊脉的大夫。
老大夫探了会儿脉,转问:“夫郎这症可有多久了?”
书瑞听得大夫问,见人严肃的面孔,一时也紧张起来,老实道:“倒是前些时候正月里偶也有胸闷略反胃的时候,独今朝吃了油饼,这才症状明显些。”
“可有觉冷、嗜睡这般?”
书瑞动了下眸子:“前头落雪,是有如此。”
老大夫疏而展颜:“那便是了,夫郎有近三个月的身孕了,这厢竟才发觉,老夫也便问得细些。”
不敢喘大气的柳氏和肃着一张面孔的陆凌听得这话,皆是一怔,片刻后才缓过来。
“有孕了!大夫是说我们家哥儿有孕了!”
老大夫捋了捋胡须,笑应了柳氏的话,出门看诊的,最喜把着这等脉。
再次得到大夫的肯定,陆凌和书瑞皆然欢喜,两人的手也紧握在了一起。
书瑞两只眼睛也亮了起来,不可思议这忽而来的喜讯。
柳氏当真是欢喜疯了,双手合十一通祷告,接着教人预备了个红包送与大夫,好生给人送了出去。
“谢天谢地,俺们陆家可算有孙儿了。”
晚间柳氏张罗了一桌子好菜,陆爹和陆钰回来都有些惊奇,说是有甚么喜事弄得这样丰盛,得听书瑞和陆凌有了孩子,两人皆是大喜了一场。
陆爹高兴的不比柳氏少,喊着陆凌,教人好生的照看着书瑞。
一家子人乐得跟过年吃团圆饭似的。
“真就有孩子了,先前怎盼都没得动静,倒不想放平整了心,说来便来。”
夜间,书瑞躺在床上轻轻的摸着自己的肚子,已经高兴了一下午,却也还未完全从喜悦中抽出身。
他扬起眸子同陆凌道:“原是早有些征兆的,我说怎怕冷贪睡,又还觉自己胖了的,不想是有了孩子,咱俩当真也是心大!”
陆凌也将手覆在了书瑞还没见隆起的肚子上,眸光可见的多了些为人父的柔和,他也虚惊了一场,幸是人贪睡又怕冷的,两人没似从前那般胡闹,要不得身子不适,可不堪设想。
“原也是因头个孩子,往前又没得生养的经验,难免疏忽大意了些,只以后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了。”
书瑞听这话,拍了陆凌的手一下:“还头个孩子,怎的,你要几个孩子?”
“自然是有几个都好。”
书瑞抿嘴笑起来,问陆凌:“那你希望是小丫头小哥儿,还是男孩儿?”
“我没想,总之是男孩儿女孩儿我都喜欢。自然,若是小哥儿或小丫头最好,娘总念叨没得个哥儿和丫头,要得了,不知得心疼成甚么样。”
陆凌光是想着以后宅子里要有个小崽子跑动来跑动去,便已觉心里发软了。
书瑞心中充盈的眯起眼睛,总觉幸福好似愈发有了实感。
三月春光融融,柳枝抽了条,榆树也焕然得新。减去了些厚重衣衫的书瑞,觉是整个身子都轻盈多了。
春日的风拂过脸庞,很是轻柔,风里有一股春时新生的气味。
书瑞看着坐在他身旁的俊气男子,眉骨高高,鼻梁高挺,岁月流走,这人却还一如当初他头次见时的好样貌。
春光洒下,暖而不躁,洋洋洒洒的落在了陆凌身上。
书瑞坐在阴凉处,微眯起眼睛,他觉得怪得很,阳光分明在他的身上,怎自己却觉得分外的温暖。
“陆凌。”
“嗯?”
“春光这样好?你怎不看我?”
陆凌闻言,收回眺望远处的目光,转过头看向书瑞,他眸中有笑,未做言语,须臾,代替他回答书瑞话的,是陆爹气急败坏的声音。
“陆凌!你这臭小子,把瑞哥儿带到那样高去是要吓死谁!还不快给我下来!”
书瑞听得屋顶下头传来陆爹的声音,眸子微睁,险些踩碎了瓦片:“爹今儿怎这样早就下职了?”
陆凌小心握住书瑞的手:“谁晓得他的。”
他探出些头,同屋顶下的人道:“带你孙儿晒晒太阳,你声音再大些,要教你吓着了!”
——正文完。
第103章 番外1 孕间事
书瑞自打教大夫诊出有了身孕以后, 害喜便有些厉害。
他虽历来不把自己看得多娇贵,可有了身子,发觉却是由不得自个儿不娇气。
素日贪睡, 一日里头晚间睡得早,早间起得晚不说,午间还要睡一场。
从前本还不差的胃口,时下是吃甚么都不大对付, 闻着些荤腥就害口, 要不止止,得真吐出来。有时别说看着吃的, 就是想着胃里也翻腾。
陆凌见他厌食,怕他身子吃不消,要么去自家客栈的灶上, 喊晴哥儿跟徐诚治些适宜有身孕人吃的小菜, 要么就留心听着旁人说哪家食肆, 哪处馆子的菜好, 他前去买了打包回去,菜肉、糕点、果子,总之是变了花样的往家里带, 就盼着他能多用两口。
书瑞也晓得陆凌有心, 尽可能的哄自己吃些,只许多时候实不成事,好送进口里才觉不舒服,不好的连见着就掩了口鼻别过脸去, 直喊拿走拿走。
却偶时又怪,忽得嘴里馋一样吃食得很,这般状况不分时候, 白日有,夜里也有。
本有了身子多眠,可逢着馋嘴的时候,竟就睡不着。有一回夜里,陆凌都吹了灯搂了他睡下,他窝在人怀里,就想吃些辣口的菜,尤其是想着那酸酸辣辣的鸡脚子嘴里就直咽口水。
书瑞闭了眼儿,想着没得大半夜的还胡乱要吃这些东西的,给人晓得了当真是要觉他能作怪得很。
他哄着自个儿说睡着了也就不想了,思想能受他理智的哄,嘴馋却不听招呼,折腾的他都睡不安枕了。
陆凌抱着人,见他睡得乖巧,一动不动的,可呼吸却乱得很,依着往常,吹了灯没一刻钟呼吸就平稳了,今朝却浑不似那般,便问:“怎的了?”
书瑞觉不好说他想吃酸辣鸡脚子,只道:“没甚么,想是午间歪在榻上睡得时辰长了些,夜里睡眠就少了。”
陆凌却再晓得他的性子不过:“你如今有了身孕,本就不好受,有甚么要与我说。”
书瑞听得他这样说,心里觉暖,依着他怀里,有些撒娇又有些无奈的小声道:“不知怎的,倒是忽而有些想吃酸辣鸡脚子了。”
“这时间上怕是食肆都打烊了,家里头又没得鸡脚子。”
陆凌想了想,道:“我上夜市上去给你看看,说不得能寻着。”
话罢,人立就起了身。
书瑞看他动作好不利索,眨眼的功夫就已经从暖和的被窝里下去了,倒春寒的天气上,被窝都睡暖和了却给叫着再出门,少有几个有这般毅力肯出去的。
陆凌一头穿着衣裳,一头与书瑞道:“你安心在床上躺着,我翻墙出去不走大门,不会教爹娘晓得。”
书瑞想拉着他,喊他说这样晚了就算了,出去未必能买着不说,白受些冷风,他的胃口又变化的快,说不得一会儿又不想吃了。
陆凌却言想了一刻都是好事,总比他甚么都不想吃要教他安心些。
说罢了,将坐起身的书瑞给塞回了被窝,转轻声出了门。
殊不知陆凌出去,外头不仅起风冷,竟还飘着绵绵的春雨,当真是春寒料峭。
这冷雨夜上,便是夜市出摊儿的小贩都不多,一连跑了南城和东城的夜市都寻着有酸辣口的鸡脚子,也还不死心,又往西城那头去,到底是教他在一家卖羊脚子的小摊上找着了鸡脚,偏却只有卤香的,陆凌给多使了些钱,硬央了摊主给新鲜做了酸辣鸡脚。
鸡脚子放在舂桶里,除了辣料,又切了小酸橘进去捣,味道给弄得酸酸辣辣的,陆凌才满意的拿了回去。
书瑞等得了这一口馋嘴,嘴里直淌口水,取了筷儿来吃,却也只就得吃了两口下肚,一下就不对味了。
陆凌出去没拿伞,又还跑了大半个府城,身上和头发都似撒了层白糖似的,取了帕子来擦干,回头就见着书瑞又要作呕,连倒了水给他吃,轻轻顺着背。
虽是周折买来的吃食没动两口,好在馋解了,总算能睡得着了。
书瑞教肚子里的小崽折腾,却也没少折腾陆凌。
早先是吃食上变得娇气,后头些不单是闻着荤腥不好了,就是嗅着不对付的香料也得犯恶心。
开春后天气见了些暖和,陆凌每日在外头跑得多,不是汗便是尘啊土的,接触外头的人也多。
晓是书瑞爱洁净,又从隔三五日就要来给书瑞看脉的大夫那处听说,哥儿有了身孕后身子要弱些,春月里头病气流窜,稍不注意就容易染上些病症,为此他担心把外头的病气带回来过给了他,便格外留心,每日回家头先都要去洗浴了再跟书瑞亲近。
一日里,因着屋里的澡豆使完了,陆凌就教下人给临时取了些来用,本还想着将自个儿拾腾的干净了才到书瑞跟前去,不想还没触着人,书瑞便捏着鼻子,直说闻不得那茉莉的香气。
陆凌也不敢似从前一样生是去抱住人,只得赶紧又叫了些水把身上重新洗了一遍,直教是再闻不着气味才作罢。
且这犯恶心,也并非是从前闻惯了的气味再闻着就不会又不适,纯然说不清,有时是没常闻的香料气闻着会恶心,有时却是常用的闻着都不好。
为此能规避的尽量规避,若没规避着的,一觉不对了就赶紧给撤走。
书瑞看着陆凌甚么都对他无有不依的,心头既是感动,却又愧疚,两种情绪时时给交织着,教他觉纠结。
从前没有身孕的时候,他性子挺是克制的,便是晓得陆凌对他好,却也不会多任性,总相互体谅着。
可有了孩子以后,他便觉自己的性子也开始变得怪得很,一些琐事小事儿就能教心里头不舒坦,觉委屈,爱多想。
这日,书瑞起身来,肚里空空的,就又觉恶心,陆凌去取了些粥食端来了屋里头给他吃。
为着他好受些,陆凌去问了大夫不少关于害喜的事,以及如何应对。
听得若害喜症状严重,最好便是少食多餐,每隔个一两时辰就吃用些食物,为此陆凌特意吩咐了家里灶上,时时都得有吃食才成。
且多备用淡、凉些的食物。
教陆凌给悉心照看着,书瑞觉害喜比从前稍好了些。
书瑞在桌儿前吃着粥,见陆凌去开窗通风,听他说通风好些,不易闻着不好的气味犯恶心。
他道:“我觉大夫诊脉说有了身孕前,虽也有一二孕症,可却没似诊后这样厉害,是不是我总在家里待着,也没得多少事,精力都在有孕上,反还症明显了。
要不得我去铺子上坐着算账,与客人说说聊聊,分散了注意,说不得还好些。”
陆凌闻言,过来陪着书瑞吃早食,温声道:“铺子上人进人出的,你又是个眼里有活儿不爱指挥人的,到时去见了活儿就做,说不得将自个儿累着。”
书瑞听得陆凌这话,心头就有些不大欢喜了:“这厢还能走能动的,我也不觉身子笨重,怎就去不得铺子上了。”
他放下了勺子,竟生了脾气:“一点不好,在家里不是吃便是睡,谁人都有事情能做,偏我是个闲人,还得闹腾着你们照顾。”
说着,书瑞便鼻子发酸,眼睛也红了起来。
陆凌打和书瑞认得起,就没见着人哭过两回,这厢不过似往常一般的语气说了两句,怎就伤心了起来。
他登时有些手忙脚乱的放下碗碟,连安抚人:“我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是真管着你不教你出去,你想要到铺子上我一会儿便随你去。”
书瑞见陆凌慌乱的模样,更是伤心,一头埋在桌上哭,他心里不是滋味。
原本也晓得陆凌不是个巧言令色,终日将甜言蜜语挂在嘴上的人物,说话时总直些,可将才人也没凶没恼的,不过是没顺他的话说,偏自不知怎就往牛角尖儿上钻了。
稍静下来一想,就知是他自己不好。
再想着这些日子怀着孩子是不适应,可却也没少把陆凌折腾,人甚么事不是对他百依百顺的。
书瑞知道他的情绪有些问题,可却也不似以前那般好控制,越是如此,他才越难受。
陆凌瞧着书瑞哭,又是心疼又是心慌,恼自己没事说那些话做什麽,赶忙哄着将书瑞扶来抱到怀里,轻轻与他顺着背:“是我不好,怎的都成,你可千万别哭。”
书瑞埋在陆凌的怀里:“却也不是你的错,是我瞎闹腾,怪不得你。”
“我总想着你白日要忙生意的事,时不时还得回来看看我,晚间也不得好歇息还要悬心仔细照料着我,我心里过意不去。”
陆凌听得话更不是滋味:“怎这样傻,你怀着孩子本就受了许多的辛苦,不比任何人轻松,我日日都看在眼里头,心疼得很。
我既不能与你分担这生育的苦楚,照料好你难道不是做丈夫应当的麽。孩子是你的也是我的,我出再多的力都不为过。”
书瑞情绪脆弱,受陆凌一通好哄,又觉好了很多,当真是跟吃东西害口一般,没得个定数。
遭此一遭,他心道真到了自己为人父母,才晓得了父母生养个孩子何其不易,一时间心中只更为的爱戴和感恩起自己的爹娘来。
却也庆幸自己没有看错人。
常听人言,成婚生子时才能够真正的看清些一个男子的秉性,不乏是婚前恩好的夫妻,在孕育孩子时男子才暴露其不好的本性,致使许多女子哥儿心灰意冷。
难为陆凌在这时候也不改相好时的性子,对他只有更耐心更包容的。
书瑞靠在陆凌的怀里,抽噎着说,要一辈子都跟他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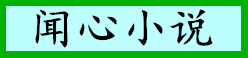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