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廷从圆圆的舷窗往外看,几辆黄色的行李拖车排成长龙,穿荧光背心的地勤人员来来回回地跑。远处能看见航站楼的轮廓,像一艘搁浅在夜色里的邮轮。
走的时候是晚上,现在北京时间应该是明天上午了。可纽约还是深夜,黑漆漆的天,时差这东西真邪门,横跨半个地球,好像太阳追着他屁股跑了一整天,愣是没追上。
姐姐的“为国争光”犹在耳边,项廷已经茫茫然置身于世界第一大都会——纽约肯尼迪机场汹涌川流的人流之中了,抬头望那穹顶高得能起飞直升机,项廷仿佛快进了一个世纪,电子屏幕上的航班信息哗哗地翻,北京站候车室还在用翻牌器,而且人家这大了十倍,亮了十倍。
这世界幕布一拉,布景忽喇喇一下全换了,就这么稀里糊涂。
这个星球上最繁华、最自由、最疯狂的地方。现在他站在这儿了。
一般人初到美国,都有种下乡人进城的笨拙,甚至一下子残废了。首先必然长时间陷入一种半聋半哑的状态,别人是英语听说两项不行,项廷是读写都抓瞎。
比如飞机上便要填的入境海关申报单,项廷一开始睡着了没拿到,睡醒了见别人都有的东西他没有,举手说他得有。拿到手,cbpform6059b,只认得6059。于是雅贿旁边亚裔面孔的女士代填,女士只有一只铅笔,斟酌完自己的刚要填项廷的时候,项廷已经要到一份中文的表。大伙咬着笔头,还在跟自己的英文表较劲呢,项廷早早交了卷。
送表申报、排队入关后,项廷找不到托运的行李了。
迷宫一样的大厅里,同机抵达的访问学者团也正东张西望。项廷双手插兜,溜达两圈,忽然发现一个事儿,日文里有中文啊!
寻摸到服务柜台。他没先问自己的行李,而是折返将会英语的学者团领来,工作人员把他们的问题一块打包解决了。学者团的人还跟项廷连连道谢。
别人提心吊胆,项廷却是如此之达观,与生俱来尤其自信。他打小就是这个性子。怕的东西不多,好奇的东西不少。当兵那几年,最盼的就是有仗打,结果天天就是训练、开会、写思想汇报。和平年代干什么都让他提不起劲来。出国对他来说是一场华丽冒险,换个地图重开一局。
美帝,刺激!英语?英语这东西只要是个人逼一逼就逼出来了,他又不蠢。
迈出纽约客生活的第一步,得先找到他的姐夫。
姐姐特意交代过,你姐夫会提前一小时来接机。你朝人群里一眼抛过去,那个最有风度的华人绅士,就是他了。项廷问长相,姐姐说成功的人都不丑。
机场大门堵得全是人,项廷特意等这一批旅客走干净了才出去,搜寻范围就小了很多。余下来接亲友的中国人里,举着的牌子没一个写项廷的名字。
忽然人群里有个中年男人冲他招手,穿着西装,笑得挺热络。
项廷撂下行李,站直了,单手往帽檐上一搭,潇洒地向外一甩,一气呵成行了个美式军礼,好像西点军校的模范生,军教片里剪出来的。都给那男人看愣了一秒,项廷已经把手放下来,冲他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了。
“followme!followme!”
项廷被这人嘴里突如其来的英语搞懵了,姐夫难道只会说洋文?在西方呆了才多久,就高雅了,可不能冒昧。他把帽子往后一推,露出额头,打量打量他。
项廷用得体的肢体语言表达了困惑,却听到男人自报家门,自称姐夫。
姐夫熟稔地接过行李就走。
刚出机场,迎面上来一个一步三晃的黑人司机,不由分说就把行李转移到了车的后备箱里。
项廷还没坐稳,车子已经滑入机场外的车流,进了隧道。隧道的尽头还是隧道,转弯,上坡,再转弯。项廷开始觉得这辆车不是在开,是在下潜一般。
然后,毫无预兆地——视野炸亮。
车子冲出隧道口的刹那,纽约轰然亮起。
项廷往后仰了一下。五层立交桥盘绕在半空,摩天楼群直插云底,帝国大厦的顶层正放射着白光,远处世贸双子塔平行矗立。车子拐上高架。整个城市在他脚下摊开了。
东河的水面丝丝液体金线,中城的广告牌十层楼高,万宝路牛仔叼着烟,朝他眯起眼睛,可口可乐的红色霓虹淌下来,时代广场的电子屏在换画面,一秒汽车,一秒香水,一秒股票代码,刷刷刷刷。那些光打在项廷脸上,赤橙黄绿,明明灭灭,把他的瞳孔染成另一个种族。
直到项廷“得得得”地叫了停。
计价器在跳字。
50、58、66、73、80。
在发疯似的往上跳,项廷发觉事情不妙。
“停车。”
“姐夫”没反应。
“我说停车!”他让司机别管什么地方,马上把他放下来。
人是下来了,行李还在上头,项廷吃车尾气。项廷狂奔不舍,姐姐给他系的领带在风里抽打他脸。着实追了一条街,但两只脚的哪能跑过四条腿的?眼睁睁看着车子窜进了第七大道,一拐弯,没影了。
这就是美国给他的见面礼?项廷撑着膝盖直起腰,没忍住笑了一声。要不是及时跳车,下一步是不是送进诈骗集团,被扔到沙漠暴晒,打到大小便失禁,被卖去公海割器官了?
这是哪啊?霓虹招牌叠着霓虹招牌,韩文的烤肉广告,日文的卡拉ok,一群喝高了的白人女孩手挽手尖叫着穿过马路,一辆警车红蓝相间的光在他的背上扫了一下。
他抬起头,找到一块路牌。
42ndstreet.
东边是联合国总部,西边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中间夹着个声名赫赫却巴掌大的时代广场。
开门红。行李没了,姐夫是假的,项廷受了点打击,不大。证件和钱都随身揣着,不拖行李人也轻便了。乱七八糟想着事,到了时代广场。
鸽群俨然是纽约的另类市民,这里的鸟不怕人,赶它也不飞,专心啄薯条,某只颈带巧克力色斑纹的雌鸽甚至飞到项廷的头上,跳华尔兹。爵士乐手在消防栓旁吹响萨克斯,印第安人推个车,车篷布上雷鸟图腾,卖缅因州的冷水龙虾,串在红柳枝上旋转炙烤。装在桶里的法棍瞧着像缩小的金箍棒,不如城隍庙油条。走进超级市场,翻了翻货架上的价签,默默把数字换算成人民币,比预想的温和。这片土地被中国人想得太神奇了,项廷发现同胞一点民族自信都没有。他转来转去,心里琢磨着能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穿黄马甲的理货员推着车路过,项廷假装研究麦片盒上的说明,瞟着眼看美国人怎么工作。听到收银员喊nextinline,口气跟收旧家电也差不多。
项廷一直待到超市关门。深夜的四十二街,便成了纽约市最猖狂的露天性市场。
驻足观察一会,就会发现这片光影丛林万花筒般地展示资本主义的荒诞:大厦里身着正装的各国外交官整日探讨着世界和平的宏大命题;往来的商业精英们,眉头紧锁在华尔街的股市曲线、银行利率的细微波动,以及季度销售额的增减之上;而在这些锃亮的文明橱窗之下,霓虹灯管滋生的暗影里,街边林立的成人影院,三美元便能换取整夜的声色体验。商店里清仓大甩卖成人杂志,硅胶人偶摆出种种反人体工学的姿态。牙科诊所、理发店和台球馆前,光天化日之下,衣着暴露的女郎公然揽客。
是蜂也喧喧,蝶也翩翩。项廷刚在长椅上坐下来,一只手就搭上了他的肩膀:“一个人?”
他扭头。
看见一张红红白白的脸,眼影是蓝的,嘴唇是紫的,腮帮子上打着两团腮红。女人年纪不好说,穿一件亮片的短裙,腿上是渔网袜,破了个洞:“我们这儿的姑娘都盼着有人作伴呢。”
余光瞥见不远处还有几个踯躅的倩影,项廷立马猜到她是拉皮条的,僵得像块石头,沉住了气连声说了七八个no,掷地有声。
在性方面,美国60年代的流行口号是干就是了。到了90年代已变成,戴上套就是了!彼时的中国,一方面国家重视未婚青年的配对问题,另一方面,管制无孔不入。公共场合逮着动作大点的,第二天单位就收到通知,影响恶劣。戴着红袖章的纠察队专往小树林里巡,强光手电筒照脸:精神文明!精神文明!
去年夏天,项廷陪一战友去公园找对象,组织上安排的集体相亲,乌泱泱几百号人,男的站一排女的站一排,阅兵似的。散场之后俩人在湖边长椅上坐着,战友掏出根烟抽,没聊两句,远处就晃过来一老头,同志,注意影响啊!俩大男人,抽根烟,注意什么影响?战友还嘴贫,大爷,我俩这不是搞对象。老头一瞪眼:那更得注意!
“呵,你不想要这个。”那妓女嘻嘻直笑,“别在意。我这里还有许多男孩子。”
这场□□风暴才刚刚开始。紧接着,她开始向项廷描绘起同性之间爱爱的各种玩法……
项廷一个字也不理解,她涂着红甲油的手指便顶成一个犄角,模拟激烈击剑的样子。
项廷比了个6,放到耳朵边上,代表要打电话。他带了一个大哥大来,可是姐夫的号码拨不通。他怀疑是无线信号不行,那找个座机试试。刚才在超市里,他就一直借电话,连线总是失败。
妓女领着他往街边一家小店走,卷帘门拉了一半,柜台后面坐个巴基斯坦模样的男人在看小电视。女人跟他叽里咕噜说了几句,男人往柜台角落努了努嘴,那儿搁着一台老式按键电话。
项廷拿起来,拨号。忙音。再拨。还是忙音。
拨了五六遍,都是那个声儿。
妓女耸耸肩:“商店都关门了,要不去我那儿试试?”
她家公寓的楼道里静悄悄的,看样子住户们已经入睡了。红砖楼,五层,跟北京的筒子楼差不多,就是窄一些,楼梯间的灯泡坏了一半。因为治安好,好几家门都没锁。
然而,物以类聚。到了三楼,一阵令人面红耳赤的声响从虚掩的门缝里飘出。
项廷现在无暇他顾,快步接着上楼。
刚走到三楼半的拐角,一道黑影突然从那扇门里窜出来。
是个小姑娘,黑人,七八岁的样子,头发扎成一缕一缕的小辫子。小姑娘已经撞进了项廷怀里,手脚并用地往他身后躲。
房门随之大开,刺鼻的烟味扑面而来。浓浓的雾霾里,两个长毛猴子似的男人一|丝|不|挂,嘴对嘴不分你我,俩男的!
项廷大脑断了电。但是男人凶神恶煞地追出来时,他没多想。拿皮带的冲过来的时候,项廷把小姑娘往身后一拨,侧身,抬手,挡住了。他没吭声,一把攥住皮带,往回一扯。
半个小时后。项廷到达异国的第一站——纽约警察局。
警察翻着记录本,说:“你先是砸烂书架,又踹坏房门,最绝的是,你跳起一脚踢掉了挂在两米多高的天花板上的吊灯。所以你的名字是什么?brucelee吗?”
项廷路见不平,以为那两变态虐童,替天行道的过程中,小女孩跑了。遂邻居报警,项廷被指控破坏公共安全。先动手的白人倒没事人一样走了,独留下语言不通又肤色迥异的项廷。项廷知道自己现在最好一动不如一静,否则局面不但没有一点转机,反而一步一步往坏的方面滑下去。于是出示了姐夫的号码,让警方帮忙拨打。
牢房里,有个狱友把晚餐没吃完的面包翻出来,让他凑合一顿,项廷也不敢吃。饥肠辘辘熬了数个小时,胃都要翻过来了。项廷想,在这里混一夜也好,挺带劲的。只是让那两个白人孙子轻飘飘走了,实在让人咽不下这口气。
另,想到那两人光着身子干的事,项廷震撼之后只剩下一个字,吐。
漫漫长夜,辗转反侧。直到次日凌晨,他才终于被带出拘留室。
一个戴着墨镜的高大男人出现在门口。
这个男人似乎充满猜疑地望着自己,好像是在研究他的一切。男人带着律师和警察叽里咕噜交流的时候,项廷眼眯了一会,也同样在观察他。这个姐夫无疑很是英俊,但这种英俊有点太虚飘太夸张了,类似猫王一样。好像是功成名就了,挺不可一世的。机场谎称是姐夫的骗子,长得就像个奇形怪状的芒果。总之直觉加上经验主义,都告诉项廷,吸取教训,这次必须要多考察一下,谨慎再谨慎。
项廷借口去洗手间,几乎是退着出去的。出了警局大门,藏在柱子后面。镜面般的柱上幻出他的轮廓,在街对面霓虹灯的闪烁中忽明忽暗,网织、歪曲、溶解。突然一辆车来,雪亮剖开夜色,在他那倒影上碾过,那强烈灼痕般的光浪,一晃就消逝了。
车在门口停下,那个猫王走过去时摘下了墨镜,斜倚在了车边。项廷这下彻底看清了,分明是个混血的长相,他就说这个人又不是他姐夫,美国骗子,你糊弄鬼去吧!
那香槟金的车身艳光四射,驾驶座的窗子伸出一只夹着细雪茄的手,世界名瓷般精致。
馥熏恼人的烟雾在他那指尖曼舞,春风吹动柳千株。项廷感觉心好像被猛的提起,又轻轻放下。
接着他便呆望着见到,车外的男人面带微笑作出浸淫名利场的轻佻状,摘走了那根燃到一半的雪茄,无比自然地放到了自己的唇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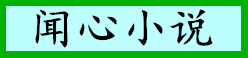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