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廷回来时, 不见半个人影,只有他的背包旁边,静静立着一面人皮大鼓。
“何叔?”
何崇玉刚要从立式空调柜后面迈出来,就被白希利一把拽了回去。
“希利!老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啊……”
“项廷会打死我的!连你一块儿……就像以前姐姐抢救室外面他……”
白希利的声音都劈叉了。一个在记忆中的模糊眼神就能把他吓死。一千多天以来, 白希利每晚都在梦中被项廷以咏春典型的连环冲捶打死, 一拳拳, 一拳又一拳, 击碎了白希利曾对项廷少男时代的深深迷恋。
他说着, 好快的一个急停, 因为低气压已经来临。
项廷不知何时绕到了柜子后面, 表情有点危险, 有点儿不可名状。
白希利的脸好像在跳机械舞。何崇玉硬着头皮, 把项廷离开这短短十分钟里, 天是怎么塌下来的说了一遍。
说那白希利第一朵金花,飘向了白如意珍宝怙主,此乃智慧护法神, 被视为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化现,其形象中右下臂摇动红檀香木制的手鼓, 这便是第一件法器了。
何崇玉说, 感觉好一般。白希利却自觉寓意不错,执意要抛第二朵。
这一抛,事情就开始走了样。
白希利口中念念有词,说什么我朋友项廷是天神化身, 四方诸王,无与伦比,求上天赐他一件趁手法宝,一定要是最关心他、最与他相配的护法神来助阵。
“东西呢?”朋友问。
白希利咽了口口水, 直眉瞪眼道:“……老大,你知道,般若佛母吗?”
项廷:“说人话。”
一切诸佛皆由般若智慧所生,故称佛母,她是坛城的核心。到了这个境界,究竟智慧已胜过一切有形法器……
说人话,就是第二抽,连个安慰奖都没捞着。
佛母想让你破空成就空空,所以,直接空了。
事情瞬间大条了。
何崇玉:“项廷,你别怪希利,手气这东西说不准。希利,你也是!要不找个看事的试试吧,是不是冲撞了什么。”
“知道了。”项廷总结,“问题不大,抓大放小,道具起辅助作用,主要看个人。然后,第三个?”
白希利已经彻底失语了。
何崇玉招手:“跟我来。”
两人来到隔壁一间房间。
动物园似的,有文殊菩萨的青狮、普贤菩萨的六牙白象、吉祥天母的骡子、白财神的龙(科莫多巨蜥冒充)、摩利支天的猪,以及十二丹玛女神三腿骡、水马、牦牛、虎……
何崇玉讪讪道:“希利抽到的是孔雀明王……”
项廷也接受了:“还行,宰了吃能暖暖。”
“是吧!”何崇玉心里终于轻松,“我也觉得,孔雀照顾小鸭子有经验,可以帮忙孵一下。”
项廷:“把鸟牵出来。”
何崇玉弯腰捡起一截麻绳,拔河。
一只羽毛华丽、神情高傲的孔雀正警惕地看着他们。
异变陡生!
一只铜锁被笼中巨兽狂暴的冲撞硬生生挣断了!
“吼——!”
斑斓猛虎如一道黄黑色的闪电,猛地从笼中窜出,血嘴滚出腥风,一口叼住孔雀!
众人两眼一翻腿一软手脚并用往外爬,青狮、白象、牦牛被百兽之王一吼彻底激怒,疯狂冲撞各自牢笼。
项廷一个侧踢踹碎玻璃反手抽出消防斧,斧柄结结实实地横砸老虎近在咫尺的大头。
这是凡人胆敢发动的攻击吗?老虎呆了下,好似突然被敲醒,真懵了。侧翻在地,四肢抽搐,连咆哮都卡在了喉咙里。
然而即便是遭此重创,咬合肌在神经失控下还是做出了最后一次反射性的紧闭。
咕嘟一声,孔雀已然入腹。
何崇玉将近晕倒:“死了死了,你别掏,啊,千万别拽出来啊!天啊天啊,这就是天意吗……”
项廷盯着一地毛看了三秒,把消防斧扔回柜子里:“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说法,你是不是人比较面,一直被当成软柿子捏了。”
他转身去找裁判。何崇玉想想还是把一根孔雀羽毛擦擦干净,插襟花一样裱在了西装的胸袋。
小沙弥仿佛早就料到他们会来,却不急不缓道:“施主,一切皆是缘法。”
项廷说:“我只信人祸。白希利扔金花的时候,旁边是不是有人故意打喷嚏、放屁?鸟出笼时,老虎笼子怎么会开着?我看了锁眼,锁舌明晃晃垂在外面。不像正经钥匙开的,手法很专业,是不是巧得邪门了?”
何崇玉补充:“对!太欺负人了!简直是八国联军在使坏!”
他表示,项廷的想象力太有限,有朵金花在白希利发力抛出的那一瞬间,在半空中解体了,只剩一个光秃秃的花托。白希利上台的几步路,有人还拉一个绊索,某人的仆人不小心打翻一壶油,还有的用一面小镜子或怀表盖反射强光刺瞎他的眼睛。
小沙弥却说:“智慧和慈悲可以互补的。在佛家看来,真正的妙法由智慧流露出来,真正的慈悲要用智慧的力量去推动。有时候,普度众生也需要小小的手段。”
项廷:“说这话你有没有觉得自个特搞笑?”
何崇玉:“常言道,杀生不虐生。你设计这种虐待鸭子的游戏,你又何谈慈悲呢?”
小沙弥却也不恼,道:“两位施主眼中所见,是人祸,是伎俩,是鬼蜮。小僧所见,却是一阵风吹散了金花,一只饿虎吞吃了孔雀,皆是因缘和合,生灭无常。这大千世界,何曾有过一刻绝对的‘公正’?今日殿堂之中,与那世间真正的贪、嗔、痴、慢、疑相比,不过是池中微澜。”
项廷:“那老虎吃了鸟的缘,缘在老虎肚子里了,你把老虎赔给我再不济赔我张虎皮?那我要是现在揍你一顿,是不是也算帮你修行了?我觉得这不叫修行,这叫欠收拾。”
小沙弥:“他日施主若真得到这份名单,肩负济世度人之重任,行于真实的人间。那里有滔天权欲、无明业火、人心反复,本身就没有一个集中的、绝对的、等待被颠覆的敌人存在,情势远比今日复杂千倍万倍。届时,种种不公、磨难、突发如惊涛来时,施主又要去何处,寻一位如您所愿、绝对公正的裁判来主持公道呢?”
项廷:“你问我到那时该怎么办?很简单。谁在搞鬼,我就把谁的手剁了。谁在挡路,我就把谁的腿打断。我知道你是谁。”
小沙弥:“施主尽可以去杀。只是你在此与我争一刻之短长,恐怕另有缘法还在改变。”
意有所指的话让项廷心中一动,他立刻快步回到比赛场地。
一眼就看见白希利正蹲在那个装鸭子的篮子前,背影透着慌乱。
白希利猛地回头,手里还捧着一只连站都站不稳、绒毛稀疏的小鸭,脸色煞白:“我…有几只小鸭子腿断了,我试着接一下。”
项廷低头一瞅,这才看清鸭篮里的惨状。
篮底挤着一堆明显是残次品的鸭子,它们有的腿显然被人为地折断了,有的羽毛湿漉漉地黏在身上,冻得连叫声都发不出,只剩微弱的抽搐;还有的干脆翻着白眼口吐白沫,眼看就要不行了,不知遭到如何加害。
项廷甚至不用问,他抬起头,看到旁边不远处的那伙人,正得意洋洋地清点着他们篮子里那些毛色鲜亮、膘肥体壮的优质鸭子,叽叽喳喳,喧天热闹。
“哟嗬!来来来,大伙都来开开眼!” 安德鲁戴着墨镜得意地出现在对家,伦敦老家摇到人了以后他很硬气,在人堆里也有个人模样了。
用脚踢了踢项廷他们面前的鸭篮,夸张地捏着鼻子,仿佛闻到了什么臭味:“你们管这个叫鸭子?我看是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瘟货吧!”
白希利穿个黑色漆面的羽绒服,背后看确实像个垃圾袋,站起来:“你们这是作弊!你们太无耻了!故意把好的都挑走了!”
“无耻?这叫智慧,你这个没脑子的反骨仔!跟着我们混了那么久,就只学会哭爹喊娘吗?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天经地义!强者,就该配上强壮的鸭子,而你们这些渣滓……”
安德鲁伸出手指,逐一点过何崇玉白希利和项廷,一个一个数过去:“一个痨病鬼,一个小鸡仔,进去别直接冻硬了!一个哈巴狗扎了个狼架势,丧家犬!吓唬谁呢?再看看你们的法器:一面破鼓,一根羽毛,还有一个……哦我忘了,什么都没有!哈哈哈哈!绝配!真是天造地设的绝配!”
白韦德颤颤巍巍地帮腔:“阿弥陀佛,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啊!施主,你看到了吗?孔雀被食,般若成空,如今连众生都在唾弃你!你逆天而行,神佛共愤啊!”
白希利屈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愣着干什么?”项廷指令清晰下达,“木片,最细的。布条。何叔,热水,干净布。”
何崇玉:“啊?这……这都什么时候了……”
“能活一只算一只,骨头断了,就得接上。”项廷说,“既然要接,就好好接。”
众人见无趣,渐渐散开,各自去做上场前的最后准备。
因着伯尼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八国联军联合起来了,紧紧团结在米字旗周围。
先把名单从和尚那里拿过来,后面怎么瓜分,再说。
白希利一边给鸭子做着手术,一边忍不住很丧:“全是我的错,我老是拖你们的后腿,我去死好了!”
项廷没看他:“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正常。”
白希利:“都这样了……还比什么呀?直接认输算了。”
“见招拆招,两横一竖就是干。”项廷目光像雷达一样锁定着场中那些虎视眈眈的对手。
何崇玉搓着手焦虑:“希利也是,当时怎么就没硬气点拦住他们呢?哪怕多抢下一只好的鸭子也行啊……”
项廷打断他:“是我的问题,我不该走,错在我。好了,枪杆子要对外,不能对内。”
何崇玉却更急了,比划:“可是你的枪有用,别人的枪也有用。而且别人的枪,这个枪字,你最好带上引号!我刚才打听了一圈,他们弄到手的那些法器,跟我们的一比,简直是炮弹。”
项廷眼神变得锐利:“两间冰室是独立的,物理上谁也影响不了谁。他们现在玩的就是心理战。就算一手烂牌,只要打对了顺序,未必不能翻盘。”
想了想:“第一场,他们必然会派上看起来最强的人,企图在气势上碾压我们。白希利你打头阵。鸭子,你带五只最老弱病残的……”
白希利有点呆气地插嘴:“那我能自己挑吗?有几只,跟我特别投缘。”
项廷:“嗯,能撑多久算多久,你不需要赢,也不需要保护鸭子只需要保护你自己。你的任务是最大程度地消耗对方的耐心和体力,打乱其节奏。”
白希利脸很白了:“我撑不了多少时间吧……”
反正也无人可用,干脆就任人为瞎好了,撞大运。何崇玉想。
“你时间还能负的吗?”项廷却一种奇异的镇定,“记住,感觉不对就立刻放弃,我们后面还有机会。第一局让他们误判我们的实力,就是最好的开局。这是接力赛。”
他看向白希利,目光沉静而有力:“把真正的决战交给我。”
“那、那那有什么策略吗?”
“你有你聪明的地方。”项廷肯定地说,好像深知白希利的潜能似的。
“项哥,你真的信我吗?你,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以前的气?”
“革命分工不同,你别想七想八。破坏团结的话,到此为止。”项廷活动了一下手腕,拍拍他,死马当活马医,“我教你打套军体拳吧。能记多少算多少,关键是把那口气提起来。”
三分钟后,白希利有点像芭蕾和哑剧的结合:“拜托你不要打得那么随意让我以为我也会!”
何崇玉分给一人一根羽毛:“我们三个人别开生面,插草为香,一起努力!”
小沙弥道:“时辰已至。请各方遣第一位代表,入室应试。”
钢化玻璃门被拉开,一股肉眼可见的白色寒气汹涌而出,瞬间让室温又降了几度。
那个前苏联将军“咔哒”一下捏了捏自己的颈骨,发出爆豆般的响声,大步出列,粗粝的俄语咕哝着。
然后,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脱衣服。
扯掉了上将军服,露出了厚实的军用毛衣。当他赤裸上身时,不少人都下意识地退了半步。
像头人立而起的棕熊,脂包肌肚子又大又鼓,浓密胸毛从胸前一路蔓延至后背,宛如一件天生的毛皮大衣。
众:“太可怕的基因了!简直就是一辆推土机!”
某学者:“这也太大了我的爸爸……”
众人的目光,立刻投向了另一边。
白希利也哆哆嗦嗦地开始脱,袜子都比对面的小好几号。
安德鲁在费曼身边低声嗤笑:“王弟,你看,一只拔了毛的鸡,小眼睛的麻风病人!”
两个人之间的对比不可能再大了。其余也没人笑白希利了,都不太忍看。
肉坦装甲怪物伸出大而肥厚的手:“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可以用任意一只手使劲跟我握手。”
差点把白希利捏得粉碎。
在白希利的惨痛大叫中,安德鲁笑得更开心了:“哦,可怜的小东西。”
前苏联将军从宝物堆里拿起了属于他的那一件,大黑天大黑天的酒碗。接着,他从自己靴子里抽出一个扁平的金属酒壶,将里面清冽的伏特加哗啦啦倒满了那只碗,啪!把碗一掷摔得粉碎。搞得声势很是浩大。
仰头猛灌了一大口,舒畅地哈出一口白汽,然后大马金刀地走进了左侧的冰室。
一屁股坐地上,真像个爱斯基摩人,巴适。
甚至还隔着玻璃,对外面的白希利举起碗的碎片,致意。
白希利气血两虚还没进去牙齿就打颤了:“我……我的鸭子已经不动了。”
项廷默然无话,话都在脸上:“你人没事就行。”
白希利一咬牙,张开手臂、单腿提膝,效仿白鹤亮翅的样子,赤脚冲进右侧冰室,如同赴死。
钟表匠对白韦德道:“令公子定能成大器。”
白韦德尴尬一直在笑:“侄子,侄子!”
玻璃门同时关闭。
对决,正式开始。
前苏联将军那边,时不时抿一口烈酒,甚至开始哼唱《喀秋莎》,人与鸭子尽欢颜。
而白希利刚冲进去不到三秒,浑身便疼。他的皮肤、他的骨头、他的肺……
“咯……咯咯……咯……”
甚至无法控制牙齿的撞击声。他想抱住自己,可那点可怜的摩擦根本产生不了任何热量。皮肤从青转紫,独眼不受控制地翻白。
“完了完了,”何崇玉急道,“希利是不是要休克了?这才不到半分钟啊!”
三分钟过去,白希利顺着冰壁滑倒在地,意识飘向浑沌的边界。他感到最后一口热气离开身体,逸出,呵成一小片转瞬即逝的水雾,那水珠淅淅沥沥地落回他脸上,在心里不规则地跳跃:他的人生,原就是一连串的失败、背叛和无法逃离的被抛弃……但是,就凭姐姐那一笑这趟也没白来,哪怕身入宝山却最终般若成空的戏谑结局,卧薪尝胆的三年,也就值了。曾经,那初入密宗的灌顶仪式、被迫参与的法器开光,仿佛要将他原有的灵魂驱赶出去,好让另一个东西住进来……此时的寒冷,竟让他感到一丝久违的干净。
大家到最后都会死,漂亮洋娃娃大盗姐姐也被我害得险些死去,我为了姐姐死一死也没有什么关系,是我欠姐姐的,也是一种圆满……
小沙弥给每队分发了一个通话器,告知可随时联络内部人员、交流策略。
何崇玉赶忙抓起话筒,他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胡乱想到了什么,就开始口不择言:“希利!希利,你还能听到吗?你不是要和蓝并肩作战吗?振作点!蓝沉睡,你再难再苦都挺过来了,现在他醒了,你怎么能倒下去?你不能倒!你的羽毛……对,孔雀!孔雀就是蓝变的啊!你感觉到了吗?找到点感觉没有?你手里攥着的是孔雀明王的心力!是蓝的愿望!他把愿望交给你了,你不能松手!”
项廷顺着何崇玉的情绪引导道:“你问他看过西游记没,里面的孔雀公主。”
冰室之内,白希利嘴角挂着一丝解脱的弧度,涣散的眼瞳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乌紫的手指,在胸前上摸索着,抠出了那根在胸口冻住了的孔雀羽毛。
放在眼前,一直盯着。他的呼吸似乎都变轻了,仿佛进入了某种悬停的状态。
与此同时,隔壁冰室。
“哈!” 前苏联将军嘲弄地看着对面那个静止不动的小弱鸡仔。
“嗝……”
酒喝完了。
真正的寒冷,此刻才降临。
失去酒精麻痹,将军开始跺脚、搓臂、捶胸,试图榨出最后一丝热量。但体温依旧不可挽回地飞速流逝。
五分钟后,他的脸由红变紫;十分钟后,眉须挂霜。
极寒之下,众生平等。
二十分钟:“开……开门!放我出去!见鬼了,开门!”
连滚带爬地摔了出来,差点再也爬不起来。他那身引以为傲的的体毛大衣上,挂满了冰冻的鼻涕,像个输光了的酒鬼。清点一下,三只鸭子尚存微弱生机。
白希利还在里面。
一动不动,恍若坐化。
众人低语:“是不是……冻死了?”
项廷对着联络器沉声道:“可以了。出来,你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出来不丢人。”
对讲机里,传来一个微弱、飘忽的声音:“我还行。”
何崇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希利?你没事?你真没事?”
“还行。”再次确认道。
白希利推开了冰室的门。
那些不被看好被所有人挑剩下来的丑小鸭,一!二!三!四!五!一只不落,一只不少,齐齐整整排着队跟着白希利歪歪扭扭地走了出来。
带头的白希利绊了一跤,小脚趾被割破了。血淋淋的,肉翻着,又冻上。
“来!热水!我给你好好揉揉!”何崇玉忙给他清创包扎,“你怎么撑下来的?”
“它……”白希利举起那根一直捏在手里的孔雀羽毛。
“羽毛?羽毛怎么了?”
白希利指着羽毛末端那个斑点:“你们不觉得,它特别像一只眼睛。这是我在密宗卧底学到的,他们叫‘观想’。特别是像眼睛这种有‘摄心’效果的,能帮助入定,你盯着它,它就是你的全世界。你进去了,身体就不是你的了。”
项廷:“把自己给催眠了,有点门道,是个奇兵。”
白希利用手在鼻子上一抹,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笑:“只要我躺得够平他们就无可奈何,我的专长就是睡觉嘛,没给姐姐丢脸吧!”
何崇玉眼圈都红了:“希利,如果蓝是孔雀,你就是天鹅!”
这个开局,惊天爆冷。
“不可能!”安德鲁冲到小沙弥面前,“是那根羽毛!那根破鸟毛有问题!裁判!你不检查一下吗?”
面对英王室头号被宠坏的孩子接二连三的不检点行为,钟表匠大臣说:“安德鲁王子,您似乎没有能力在脱稿的情况下拼凑出几个得体的句子,那就请停止您具有强烈戏剧性的发言吧。”
对一位王子深失所望的他,转头,另位王子也不见了。
费曼沿着长廊向前走去,尽头,是蓝珀的房间。
他的脚步不自知间越来越紧。在他八岁的生日游行王室阅兵典礼中,有人曾向他和他的马匹发射了十二枚空包弹,卫队对此惊慌失措,而幼小的他只是攥住缰绳,面色如常。
现在的他却与王室乃至整个英联邦要求的冷静相差甚远,各种迹象都表明会有一场风暴。
“殿下!”钟表匠在后,以他能接受的最快步速狂追不舍,脚后跟碰不到地面,“究竟是什么事,能让您如此失却分寸?又是什么人,值得您这般不顾体统?这样做不合适,至少于您不得体。殿下,您要么是堕落了,要么是疯了!难道您的疯狂现在就像地心引力只需要轻轻一推?”
然而,长廊中段聚集的一小群人阻断了去路,远远的偶尔可以听到人们响亮的嘲笑声。
“瞧瞧,瞧瞧,这下可好,伯尼先生,以后怎么高贵呀?”
“就皮肉伤包成这样,他总是这样没事干嚎!”
那人笑嘻嘻的,故意按着伯尼纱布下的耳朵,极尽落井下石之能事。
“行啦,上师不是吩咐了嘛,再怎么着,怎么样也得来收个尸吧!免得难看……”
原来是白韦德的门徒们,见伯尼势颓药石无医,不中用了,是人是狗都上来踩一脚。
忽见费曼王子迎面而来,这群人顷刻间溜得无影无踪。
“剑桥公爵,”看似快没气儿了的伯尼,忽然叫住他,听不出来是人类的语言了,从坟墓深处传来的,跟丧尸似的。
他因常年经营慈善形象,会打一些手语。不清楚的词汇,他就用蘸水笔漂亮地写在一张羊皮纸上,那真是一手绝难一见的好字。
“我记得,我们曾是共享午后红茶的朋友。”
费曼的目光没有在他身上过多停留,好像明白他的意思,又不明白地说:“御医会来看你。”
“伯尼先生!”钟表匠大臣赶上前,惊疑地看着伯尼手腕上那副手铐,“是谁如此大胆,将您禁锢于此?”
伯尼中了蜈蚣毒的脸五颜六色精彩纷呈,他露出一个堪称恐怖的笑,然后动了动手腕,手铐居然哐当一声自行脱落,砸在地上,根本没有锁。
他在心口指了两下:“是我,拷的我。”
钟表匠眉头紧锁:“我不懂您那种高层次的哑谜。”
伯尼抬眼向上看了一眼,目光不屑:“因为我要让项廷看到我已经日薄西山,若非如此,他怎么可能掉以轻心,放心地离开场地那么久,制造那么大的暗箱操作空间?”
费曼淡淡地道:“我认为并非如此。他去得很久,只是因为蓝在他心中的分量超乎一切。”
伯尼笑了声,又笑了声,他存心让话里有点其他意思:“是个很客观的认识。那您至今未得伊人一见是因为您不够在乎蓝吗,殿下?”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口型无声地补上了那个词:“陛下?”
钟表匠大臣闻言色变,立即上前半步:“伯尼先生!请注意您的言辞以及您对话的对象!您应当比任何人都清楚,贵党内对您的耐心已然耗尽。一个失去庇护的人,在风雨来临时,结局往往不甚体面,昔日的盟友会划清界限,您过往的仇家想必会很乐意处理后续的事务。即便您有幸得以善终,华府的门廊,恐怕也难再为您敞开了,您此生也再无染指国家层面的权力的可能性了。”
伯尼毫不在乎继续道:“也是我让人推了白希利一把,我知道他必然会硬逞强,戴罪立功的人总是心切。若不是我这一推,你们只能干看着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归来,耍杂技一样操控那朵小小的金花,飞往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更是我,拿走了老虎的食盆,打开了锁,授意他们先去挑鸭子,是我从一开始就把项廷的船底凿穿,桨也撅了,我是这一切人祸的总导演。”
钟表匠:“您的言下之意?”
伯尼吃上一块含有大麻成分的果仁巧克力,当着两个古板英国人的面,忍不住大笑起来。几乎纵声长啸,那样子很招摇,便是所谓天赋人权的自信。
“我就不用给你们留着那层窗户纸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项廷和他的团队。我的自负虽然被项廷狠狠地踢到了大街上,但我的野心没有像下雨天的街头粉笔画一样消融。”
“第一场的失败已经向你们证明,单纯的体魄不堪一击,意志力、好胜心,尤其是知己知彼,才是决胜关键。中国有一句古话: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
“项廷,把我像婴儿一样玩弄于股掌之间,是的,没有人比我更恨他。但正因为如此,你们此刻最需要的第二个盟友,乃至战士,恰恰是一个既了解他,又狠心的聪明人……背水一战。”
钟表匠大臣盯了伯尼很长时间,心里在权衡。
方才项廷演练军体拳时那充满爆发力的画面在他脑中闪现,他不由得转向费曼,忧心忡忡地低语:“项是位武术大师。他看上去相当危险。”
“岂止,”重伤的姿态一扫而空,伯尼彻底挺直了身体,“有一件事,你们之中又有谁比我更了解,他的异能。项廷,是冷战期间美日合作研发的遥视者,代号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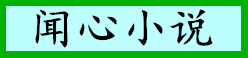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