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皇帝到长乐宫之前,一个杂耍班子正奉旨献艺。
吹火的,胸口碎大石的,走绳索的……
这杂耍班子是名震天下的,前不久刚到了长安城,就被引见给江乔。
一套把戏耍完了。
江乔微微扬了扬下巴,示意宫人去打赏,又专程叫那走绳索的兄妹二人上前。
她细细看了看这兄妹二人,看得两个小家伙身子抖在了一块。
江乔笑了,“你们走那么高的绳索,不怕掉下来?”看到她,却那么怕。
没见过几个“贵人”的小孩子听不懂她的言外之意,真以为江乔在问绳索。
个子高一点,也瘦一点的兄长开了口,“不怕,这绳索看上去细,但踩在脚下是实的,我们走惯了。”
江乔一怔,那班主见状不对,想上前给两个小孩开脱,还没说话,江乔摆了摆手,回答,“我知道。”
绳索是实的。
路是能看到的。
还有兄长在一旁,大手牵小手,其实不会怕。
她没再说什么,只给这班主又单独赏赐银钱,就叫他们下去。
有了这一笔钱财。
且进宫得了太后赞赏的事迹。
这个班子的来日,或许会更t加红火。
但都与她无关。
小皇帝到了,他一个人走了进来,又规规矩矩跪下行礼请安,她看着,也让宫人退下。
这将是母子二人第一次面对面谈话。
不用外人在场。
江乔凝视着他,小皇帝安静起身。
“母后,可有要事同儿臣说?”他轻声问。
“你打算怎么处置罗慧娘?”江乔也问。
小皇帝眨了眨眼,唇瓣微微张开,似乎在思索该怎么回复。
但他不该回复。
那女刺客,还只是女刺客,长乐宫刚刚下旨,让大理寺负责追查此事,“罗慧娘”这个名字,还不到能够传播的时机。”
“是你。”江乔不等他做出反应了,她漫不经心地一锤定音,认定了这事背后的主谋。
“母后……”小皇帝支吾了一声,仿佛没听懂她的话语。
想着如何解释。
江乔只是望着他,无笑也无意,这是一双熟悉至极的眼眸,他曾在数个深夜,点着宫灯,在镜中望过这双眼。
但还是有所不同。
随即,小皇帝恢复了平静,他笑了笑,又是一声“母后。”
不同语气。
“您是怎么发现的?”小皇帝半是虚心请教,半是无所谓地好奇。
这是他自儿时就懵懵懂懂勾勒出的计划,罗慧娘的出现的的确确在众人意料之外——她太微不足道,无论是她个人的意愿,还是她的悲惨经历。
但意料之外的出现,常常有着出乎意料的作用。
罗慧娘,老王爷……一环扣着一环的算计,小皇帝自始自终没有堂而皇之地出面过。
他以为,他始终安然无恙地缩在了那个怯懦幼帝的罩子里头,并没有露出太多的马脚。
忽地,他拉长了尾音,恍然大悟地“啊”了一声。
“是因为老王爷吗?”
一位几乎与世隔绝的王爷,无缘无敌的,为何要掺和到这乱事之中?
“还是因为……”小皇帝望着江乔,没有等到回答。
因为这个答案,并不重要。
江乔目光淡淡地扫过去,倒不意外小皇帝露出了这幅真面目,她只感慨,从前觉得小皇帝像萧晧,像江潮生,有着所有人的影子,仿佛是一团任意搓圆的面团,可如今一看,她发现,他最像她。
她生的孩子,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她的阴毒。
她只问,“你还有什么算计?”
小皇帝来了长乐宫,这说明,他还有话同她这位太后、母后说,无论是好话、歹话、实话、谎话,既然有话能说,这一局就不算到了尽头。
看着小皇帝,再一次一寸一寸打量着他,或许是因他父亲的缘故,狄人较汉人总是长得快一些,而小皇帝在不知不觉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少年人的模样。
却是一个很清瘦的少年,单薄的身子套在单薄的衣裳里。
少衣少食,效仿古来贤人,这是他那些老师给他定下的规矩,说是要以此锻炼他的秉性。
但怕冷好暖,也该是每个人的天性。
江乔承认,她一直不懂她这个孩子,但她懂得年轻时的自己。
“开门见山吧,告诉我理由,然后说出你的目的,你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地来长乐宫,也无需再惺惺作态,浪费你我的时间。”
她的态度很明白。
她不怕事,她从来没有怕过事。
但她也不会白白被他利用。
小皇帝又一次握紧了拳,再松开,目光落到了江乔腰上的玉佩,眸光微动。
母不知子,子又何尝知母?
但有些话,必须推心置腹地说。
“母亲,这是我登基的第六年了。”
他少年早慧,可越是早慧的人,越是难得糊涂。
“您是我母亲,您坐在这龙椅上,我无话可说,但江先生……他算什么?”
“太傅……他装模作样地只给自己一个太傅的名头,可谁不知,朝中六部,二寺,三司都有他的人!太傅,太傅……可母后,你可知百姓是如何说他的?”
百姓不知有小皇帝,只知有江太傅,还有人张冠李戴,错把如今的皇姓,误认为“江”。
“母后,这是我的大梁。”
还是有话未能说出口。
他早早就发觉了,在无人之处,江乔和江潮生二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一点的心有灵犀让他们的争锋相对都成为了一种调情的姿态。
他恐惧。
江乔从不亲近他,江潮生在朝中只手便能翻云覆雨,若有朝一日,江潮生真的要谋逆,母后会站在他那边吗?
母亲会保护他吗?
他不知道,也不敢赌。
但他现在,只能赌。
江乔冷不丁问,“他现在在哪?”
江潮生。
小皇帝安静了片刻,答,“西山。”
此事,他连老王爷都没有说,他知道自己做得大胆,可长安城中,到处都是江潮生的人,唯独把他困在西山,他才有徐徐图之的可能。
江乔没有回答,静静盘算着。
“母后……罗慧娘的事,是能解决的……毕竟,您和他,并不是亲兄妹。”
真正的前朝余孽,只有江潮生一人。
真正该被千夫所指的,也只有江潮生一人。
江乔听着,抬起眼,再次看向他,“这便是你一开始的计划?”
小皇帝默默点头。
如若计划一步步推进下去,罗慧娘的口供中会牵扯出二人的身世。
但此刻,罗慧娘还在江乔手中,此事看似是陷入瓶颈了,但她迟早要把罗慧娘交出去。
“好本事……”江乔真心实意赞了一声,但她的称赞不值钱,尤其是在眼下。
狄人勋贵与汉家世族,因有了江潮生这个共同的敌人,被小皇帝笼络到一处了。
再细究,该是在秦将军一事上,小皇帝就开始了他步步为营的算计。
只剩下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瞒过他的?”
江潮生是小皇帝的老师,二人算是朝夕相处。
江乔不了解小皇帝,还情有可原。
但江潮生在识人一事上,有着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天赋。
该全盘托出吗?小皇帝还在犹豫,最终,他还是吐出了一个名字,“张灿。”
宫内宫外,都知道他是江潮生的人。
所有人都忘了,他自幼侍奉在萧晧身边,若无先太子的提拔和赏识,他早该死在无人知晓的角落。
他也是个太监,有着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心思。
而这位伺候过先太子,先帝,小皇帝的太监,不在此处。
江乔目光扫过,寻着人影。
小皇帝抿着唇,一不做二不休,继续交代。
在半日前,张灿奉了旨,去找罗慧娘,就算江乔此时要派人阻拦,也来不及了。
这是一个临时起意的,声东击西的手段。
江乔愣了愣,很快又笑了一下,笑容是转瞬即逝的,小皇帝凝神静气,并未错过她面上丝毫的变化,也久久没有等到下文。
他是破釜沉舟了,不是有勇无谋,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无回头的可能。
他不想和江乔撕破脸,希望母后理解他,希望她站在他这边,他是帝王,史书中记了君臣相和,也说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可江乔不言不语,那双黑色眼眸再次藏在了阴影处。
粗制的玉佩上映着点点烛光。
“母亲……”
其实他无话可说,正如江乔在这夜认识了他,他也在这一夜认识了江乔。
没有人能改变她的心意。
除非,这是她自己决定的事。
直到天亮,谁也没多言,谁都没再开口相劝,小皇帝离开了,江乔一人静静地坐在原处,视线扫过了腰上的玉佩,然后掠过。
小皇帝的话,她都明白。
他的矛盾和纠结,她也看得明白。
因看得太明白,让她不得不又想起了自己。
她想起了那一日,得知了萧晧对她的势在必得,江潮生对她自以为是的算计,哭着,闹着,嚎叫着,歇斯底里着,她将自己一寸寸剖开,看似是愤怒至极,要同归于尽,可说到底,是一点恃宠而骄般的下赌。
赌情谊。
赌心软。
当时,她以为自己是赌输了。
所以,要让小皇帝赢吗?
这时,又有客人来了,是一个久未相逢的客人。
“温昭。”江乔唤出了他的名字。
温昭望着她微笑,又停在不远不近处,“臣温昭,见过太后娘娘。”
上一次二人见面,她还是小小良娣,那一日温昭来找了她,向她要了两个承诺。
其一,她已经做了。
“我以为,这一次,你还是不会掺和。”江乔轻声,带着熟人之间的随意,可事实上,二人分离的日子,已有十年。
在南边的十年,让他褪去了文人的青涩和秀气,沉淀着岁月的沉静与安宁。
让江乔几乎生出了几分嫉妒。
“早不来,晚不来,现在来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她抱怨似的,但话是如此说的,心中却是安定了许多。
长安城是一滩浑水,其中鱼龙混杂,人人皆是各怀心思,今日是倒向了东边,但明日又说不准向往哪边,这也t是这些年她一直不过多掺和朝政的原因。
而温昭,这人容貌是变了几分,可不见得会有多少长进,肯定还是那个刚直不阿得让人无可奈何的家伙。
她信的过他。
“方才,臣已去拜见过陛下。”温昭道,言下之意,便是已弄清这纷乱错杂的局势。
“所以你是替他来当说客的吗?”江乔随口地道。
“是。”温昭微笑,“太后娘娘还记得与臣的约定吗?”
其二,促狄人汉化,稳大梁江山,为百姓生计。
“这是极好的时机,江白这些年所作所为,纵我不在长安城,也听闻了几分。”
“眼下,朝中官员不分狄汉,皆有意锄奸,借此时机,陛下再整六部,不是难事。”
江乔微微蹙着眉头,没说一个“好”或“不好”,仿佛还在顾虑什么。
温昭轻声细语说了下去,“我知晓,此事纷乱,陛下看似一言不发,可也有意集权。”
江潮生倒台后,江乔势必要被牵连,到那时,长乐宫不一定还有今日的地位。
“但也无妨,两全其美的法子,不是没有。”
只是看她愿不愿意。
温昭最后所说的话,还久久未能散去,江乔想着,再一次来到了西山。
这是一处不新不旧的宫殿,殿外枝繁叶茂,殿内却是阴冷湿寒。
江潮生一身单薄白衣,面北而跪,像是穿着丧服,为谁悼亡。
“嘎吱——”一声开门声,一道余晖映在殿中,江乔走进,停在他身后。
“滟滟,你来了。”
“兄长。”
江潮生没有站起身,轻声问,“外边是何种情景了?”
“不好。罗慧娘已经到了牢狱中,她是巴不得被拷问的,她恨我,也恨你。”
“你该知道了吧……”江乔低声。
江潮生不言语。
江乔又问,“你还有什么法子?你是算计人心的高手,我总不觉得你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他轻笑,“你愿帮我吗?”
她手上是还有几个可用之人,这次,换作江乔沉默。
江潮生声音很轻,像是从远处飘来了一阵风,可门窗都被关紧了,根本无风可入,江乔想到了多年前途径的破庙。
那破庙,才是四处灌风的。
他说,“滟滟,这些日子,我总想起过往。往事一桩桩闪过,故人一个个出现,我以为自己回到了过去,还是大周时,还在宫中,就你和我。
他说着过去。
带着一点将死之人的坦然。
……
他果然猜到了。
也无需她大费周章解释,江乔安静地听着,听着他静静地追忆。
记忆犹新。
遗忘,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尤其是当往事刻骨铭心时。
她平静地发现,她还是没法对江潮生下死手。
温昭给了她法子——大义灭亲。只要她先声夺人,私下处决了江潮生,这件事便无法彻底闹大,而她依旧是垂帘听政的太后。
可正如多年前,她没法将那碎瓷片送进他的胸口,如今,她也没法绝情地让他去死。
他不是萧晧。
他是她的兄长。
在她还未看清这个世界时,他就出现在了她身边,十多年的紧密相依,十多年的若即若离,他几乎主宰了她的命运,好坏由他,喜怒由他。
他教会了她爱,也教会了她恨。
但是,恨一个人和爱一个人一样,都让人疲倦。
所以,她沉默。
江潮生看向手中的碎瓷片,经了多年的摩擦,其边角已不够尖锐。
还是不舍。
“滟滟,世家盘踞长安城数百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铲除,但归其缘由,不过有二……”
“大梁立朝,多因狄人勇猛……”
他把她当做了小皇帝,将朝政之事,一点点揉碎了,一点点展开了,铺在她面前。
仿佛笃定了,她会听他的。
但这是垂死之人的最后言语,江乔没有打断——他们是有如此的默契,她知道,他心存死意,只太怯懦,不敢赴死。
正如他早知她有杀心,却太犹豫,未有契机。
小皇帝还是低估了他们——一个罗慧娘,实在不算什么。
真心想活的人,姿态可以狼狈,而再狼狈的样子,他们都在彼此的身上见过。
况且,想让一个百里之外的人,神不知鬼不觉来到长安城不是一件容易事。
就算罗慧娘意志再坚定,也挡不住风雨的吹打和贼寇的觊觎。
必然要有人在暗中相助。
且这人,能在朝中一手遮天。
这是江潮生给自己选定的结局。
还要说什么呢?
小皇帝渐渐年长,势必要收权,但朝野内外,无人可信,唯有生母与他血脉相连,荣辱与共。
至少十年,处理政务绕不开长乐宫。
天气渐暖,她又是个急躁性子,要少思少虑,要珍重身子。
小皇帝像她。
连握拳头的小习惯,也像她。
他……
“滟滟,对不起,这句话是早该说的。”
江潮生还是背对着她,但她想,他或许是微笑着的。
“真的,很对不起。”
……
除此之外,再也无话可说。
二人今生已是如此了,又如何许诺来世?
他们注定是有善始,无善终。
当深红的鲜血蔓延至她身前,江乔才微微动了唇,“我不怨你了。”
生离不行,非要死别,才能终止这纠纠缠缠几十年的爱与恨。
他们都不再年轻。
没法再嘻嘻笑笑。
连直抒胸臆,都需要一点勇气。
转过身,西山的天彻底黑了,一盏小小的宫灯点亮了院子。
小皇帝一脸紧张地站在不远处,见她出现,立即上前,一边不动声色地往殿内探着头,一边低声说,“母后……今日朝上,有人问起江先生了。”
还是个武官。
态度强硬,又一呼百应——是打着为江潮生出头的旗号,想要浑水摸鱼。
若再不给结果,恐怕京中要大乱。
不等他继续说下去,江乔已给出了答复,“他死了。”
小皇帝的手微不可闻一抖,也顾不上装模作样,立即上前几步,果然,血泊之中,那一人的衣裳已染成了红。
看着,一时之间心头五味杂陈,看着看着,那双眸子缓缓亮了起来,他叫住江乔,“母后……”
又问,“臣子们,还等着西山的消息。”
到底只是做,而不是说。
在他们所处的位置,有时“说”比“做”有用,因为这话,是要说给天下人听的。
小皇帝放缓了声,“舅舅……他到底与母后相依为命多年。”
“试图谋逆,畏罪自裁。”
一锤定音。
这八个字,会出现在千年后的史书中。
而眼下,她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也像是一阵夜风,吹啊吹啊,吹着她回到了青葱岁月,又经了爱恨嗔痴,她被高高吹起,脚下是茫茫西山,天地万象。
【正文完】——
作者有话说:正文完结!
大家番外想看什么,可以在本章下面评论~如果有灵感就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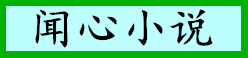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