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前颇喜杏花,故而给她起了“素杏”这个名字。
素,净白。
杏,柔美。
当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名字。
她也人如其名,渐而长成了一个柔善闲婉、贞静**的女子。
因喜音律,母亲便请来宫廷乐师悉心教导。
她既专注又勤勉,学得极为用心,不出三五载,已然小有所成。
每日坐于窗前抚瑟、吟曲,日子过得安逸且充实。
可当她偶然望向广阔无边的苍穹,也会不禁深思,到底何时才能走出脚下的这所殿宇,挣脱这处深宫,去外面的天地看一看,去见一见那未曾见过的人间烟火。
她始终满怀期待。
期待着,她虽生在此处,却不必一生都困守于此。
九岁那年,母亲生下了葵儿,也是在葵儿出生的那晚,母亲永远地离开了。
从此,她便像母亲从前待她那般去待葵儿。
教她抚琴弄瑟,教她弹词唱曲。
葵儿幼时虽有些顽皮,却也很懂事,少有无理取闹。
只是有一年春祭,见了旁的兄弟姊妹都有母夫人在一旁柔声叮嘱、问东问西。
唯有她们姊妹二人独站一处,默默揪攥衣角,这才涕泪交加地哭闹过几回。
彼时,春日灿烂,祭坛外的杏花开得正盛,蔽日遮天。
她没由来地,也想起了母亲。
想着若有来日,定要去莒国,去看看母亲口中的杏花,是否亦如眼前这般繁盛绚烂。
她与葵儿一同种下了一株杏树。
相约来年,便在这处杏树下,遥念母亲。
然,好景不长。
一日,父侯命人来传她。
她不敢耽搁,毫不犹豫便去了,却在心中暗感惴惴不安。
母亲在世时,与父侯情意甚笃,爱重深挚,十数年如一日。
可自从母亲离世之后,父侯却从未单独传召过姊妹二人。
对此,她了然于心。
只因她与葵儿都随了母亲,不论外貌身段,皆有几分相似。
怕是父侯见了,也只会勾起伤心往事,因而便也不愿多见。
殿中,父侯端坐于主案之后,案上萦绕的轻烟漫过了他初显老态的容颜。
父侯轻咳了几声,捋了捋长须,问道:“杏儿,你今年多大了?”
“回父侯,十五。”
她跪下身,恭恭敬敬地回话。
“已有十五了。”
“真快啊。”
父侯感叹道:“如此算来,你母夫人离世,竟有六年了。”
是啊。
已然六年了。
六年光阴匆匆而去,当年那个围在母亲膝下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已经悄然长成一个亭亭玉立、心思沉静的少女。
真是令人感慨。
父侯抬眼,神色复杂地看向她,半晌,喃喃自语似的道:“你与你母夫人,是越长越像了。”
她旋即伏身贴地,把脸埋低,不敢再抬。
没有应是,也没应不是。
沉默良久,终是一句话也不说。
父侯兀自又问:“葵儿呢?也该有六岁了吧?”
“嗯。”
“孤,好长时间没见她了。”
“她也与你这般,像母亲吗?”
她深思熟虑了一番,才道:“葵儿尚小,看不出许多。”
父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继而也不再说什么。
殿中一片寂静,寂静得有些骇人,唯能听见春露滴落窗扉的声音,又细又碎,似是叹息。
过了好一会儿,父侯语重心长地开了口。
“杏儿啊,人常说,女大当嫁。”
“如今你也有十五,父侯怕是留不住你了。”
她闷闷应道:“是。”
“父侯替你商定了一门亲事。”
“将你许配那齐国的公子,你可愿意?”
她又闷闷地应了句。
“愿意。”
没有片刻思索,亦没有片刻迟疑。
她极其干脆、果决地应承下来。
只因她知道,她生来便是蔡国的公主,终身大事,自是由不得她来做主。
此番,应也是应,不应也是应,又何苦再费那些徒劳之功。
倘若惹得父侯不快,即便她离开了蔡国,葵儿又该如何呢?
况且,齐乃一方强国,那齐国的公子想必也是个龙章凤姿、见闻广博之人。
能嫁于齐公子,没什么不好。
父侯见她尤为顺从,便也不再多说什么,只嘱咐道:“至于你的嫁妆,孤会着人妥善置办,纵使掏空家底,该有的一样也不会少。”
“既让你去了那齐国,便不会叫你失了体面,受人轻看。”
“是。”
“杏儿牢记父侯恩待。”
有些话,虽未言明,她却是一清二楚。
蔡楚决裂,转而投齐。
那些所谓的陪嫁,再琳琅满目、填箱盈箧,也不过是为了讨好齐国的献礼。
连带她,也是。
父侯有女颇多,之所以会挑中她,除了年纪适宜外,便是她从母亲身上多得了几分美貌。
一个只用作装点的器皿罢了,形美,足以。
“待到冬末便启程吧。”
“也好赶在春日入齐宫。”
春是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时节,能在春日入宫,自然是再好不过,因而她也应了。
“带上葵儿一起,姊妹俩也可有个照应。”
“父侯?”
她怔然望向座上之人,几不可信地道:“葵儿她……”
“随你一起去齐国。”
“请父侯三思!”
她重重往地上一磕,直撞得头脑发昏,也尤不甘心。
“葵儿才六岁。”
“明年便七岁了。”
“可……”
“够了。”
“孤心意已决。”
“不该说的,不必再说。”
说罢,蹙眉,抬了抬手,示意她走。
“是……”
她迟缓地叩了最后一头,颤颤巍巍起身,踉踉跄跄离开。
春日的临淄,果然别有一番风景。
不同于蔡城的荒疏寥落,蔡宫的潦倒凋敝。
临淄繁华鼎盛,市声盈天,齐宫巍峨深阔,气势恢宏。
春雨霏微,林苑的杏花争相盛放。
落花满径,入目皆是皑皑似雪。
她撑了一柄霜白色的伞,在纷飞的花雨下漫步。
倏忽,听见一阵悉悉索索的响动。
转头望去,却只见雨打花落,疏枝轻颤。
她回眸,再度迈步往前。
这时,那细微的声响却愈演愈烈,盖过零落的雨声,丝丝入耳。
“是谁?”
“谁在那里?”
她循声探头,这一次,恰见一线烟紫一闪而过。
却因速度过快,还未来得及看清。
仔细琢磨,似是一袭衣角,抑或是,一朵飘零的紫丁香。
踱步穿过重重树影,不知不觉,一层袍摆荡出的涟漪,缓缓映入眼帘。
抬起伞缘,那是一张清隽俊雅的脸。
“夫人,失礼了。”
来人俯首作揖,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
她赶忙收拢伞,按在腰间,也回了个礼。
“大人有礼。”
他轻声一笑,问:“夫人可知我是谁?”
她一脸茫然,摇了摇头。
“那夫人为何,称在下为大人?”
她一时羞赧,颊上生出两团红云,慌乱道:“素杏乃小国之女,不懂齐国的规矩,还望公子莫要介怀。”
“噗嗤——”
那人禁不住又笑了,问:“夫人可曾见过我?”
她仍旧摇摇头,暗自在心底回想。
眼前此人实在面生,她入齐宫月余,的确从未见过。
但,都说齐君子嗣众多,纵然未曾t见过,便是哪位公子也不一定。
毕竟,非一般人等,如何能在这林苑里悠闲散漫。
那人便笑道:“既是从未见过,那夫人凭何断定我不是朝臣,就是公子?”
“我……”
她登时语塞,面上热烫,竟显得愈发红润。
“在下同夫人说笑呢。”
他轻拂长袖,又拘了一道礼。
“方才乃是在下搅了夫人清净,还望夫人莫怪。”
咦?
方才是他?
可她分明记得,那掠过的是一抹紫。
再看他,从上到下,都是一身素净的白,几乎要和周围溶溶曳曳的杏花融为一体。
难不成,是她瞧错了?
原是雨袭了一株丁香,乱花迷眼而已。
他仍是笑,微微倾身,缓道:“在下卿族长倾,随众公子于环台读书。偶过此处,惊扰夫人了。”
她颔首回道:“小女素杏,蔡国人。见过卿公子。”
他道:“杏花夫人。”
“久仰大名。”
临淄少有雨时,而记忆中的蔡城却时常笼在绵密的雨幕中。
后来,她又在一片凄清的杏花雨下见到了他。
含着朦胧双眼,问他。
“长倾,带我走。”
“好吗?”
他面色沉郁,低低地道:“一走了之。”
“还能去哪儿?”
她的泪水,夺眶而下。
“地角天涯。”
“越远越好。”
是了,是了。
走吧。
逃吧。
走得远远的,也逃得远远的。
再也不要回来了。
离开这座金雕玉琢的牢笼。
离开这座削肉埋骨的深宫。
去哪都是好呐。
总好过,日日守着一处清寂孤寒的空殿。
总好过,夜夜伴着一具腐老衰朽的躯体。
冷雨侵阶。
飞花散乱。
可他……
可他是如何说的?
哦。
他什么也没说。
连一声都没吭。
他还是,只对她笑了笑。
亦如从前,每一回,远远相望时那样。
她本都打算好了。
都思虑清楚,也都斟酌分明了。
葵儿没了。
没在了逃离莒父的半路。
她在这世上,最至亲的人,不在了。
也再不剩一丝缘由,可以劝慰自己、说服自己,去让步、去牺牲……去赔上自己的一切,只为换来须臾的体面。
她做不到啊。
真的,做不到。
她仍记得曾在故国窗前许下的心愿,仍记得少时拥有过的幻想。
这天下之大,如何甘愿只做笼中雀。
从前,她还有牵挂。
而今,这一切,也都毫无意义了。
但他是大夫之子。
岂能说走就走呢?
她不是早就预料到了吗?
眼下,不都是意料之中的吗?
可她,可她为何?
会痛到呼吸紧促,如同针扎。
不怪他。
绝不怪他。
他身为卿族,纵然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族世代的荣耀考虑。
而她与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小国之女罢了。
留下来。
还有什么必要?
于巍巍的金台
于深深的齐宫。
可有可无。
到底是她鲁莽了、轻率了,才会如此轻易地,说出自不量力的话。
她看着,看着杏花雨下,那清绝孤直的身影渐渐远去。
看着褪去颜色、近乎惨白的残花铺落满地,被雨水的泥泞玷污。
看着几片粘在他的鞋底,几片挂在他的袍角,恬不知耻,不屈不挠。
最终,最终……
还是被不作停歇的步伐甩下,被碾碎,被踩烂……
没有了。
什么都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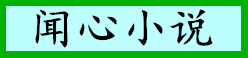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