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茵寻到柳家附近的时候,正好是柳不言成婚的日子,暗红色的灯笼挂在屋檐底下,四处张贴着红色的喜字,宾客坐在院子里吃着酒,本该拜堂的新人却迟迟没来。
苏茵戴着幕篱,并没有进到院子里,而是沿着灰黑色的墙壁,摸索到了柳家的侧门,正好瞧见柳不言和一个戴着金钗的女人在交谈。
“如今亲事已经定了,人已经娶了,现在四方宾客都来了,你还要闹什么!宗家的小姐现在都在婚房里坐着了,你要去赶走她吗?大婚之日被赶出去,你是要逼死她吗?逼死我吗?!”
“阿姐!”柳不言实在听不下去,面色涨红,“这婚嫁之事我从头到尾毫不知情,你这是把我架着,逼着我娶你看中的人。”
戴着金钗的女人背对着苏茵,但从声音里,就听出一股泼辣劲来,“是又如何,我话放这儿了,今天你无论如何,把人给我娶了,把亲成了,把苏茵和那个不知道亲爹是谁的孩子给我全忘了!以后你得记住,你已经成家了,别家的妻子,别家的孩子,你想都不要想!”
她把袖子一甩,将新郎官的衣服扔到柳不言身上,令两个丫鬟留下来,“我去前院招待一下客人,盯着他把衣服给我换上!”
两个丫鬟答应了一声,但一时又不敢上前,柳不言蹲下来,看着地上的红衣服,悲从中来。
苏茵便是这时走上前来,撑着把伞,对他道了一声,“如今,我该贺郎君新婚燕尔。”
柳不言蹲着地上,手里拿拿着新婚的红衣,仰着头,透过无边细雨和黯淡天光看着苏茵,见她一身素白如雪,站在一片天青色的朦胧细雨中,仿佛触手可及,又仿佛遥不可及。
他有许多话想说,但又不知如何说。
苏茵原本有许多想问,此刻便什么都懂了。夫妻和睦是一场荒唐,若水的生父也不是他。
他和父母一起骗了自己,但又不够伪君子,所以别别扭扭,敬着她护着她到底存着些男女之别的分寸在,怕她怪罪,怕她想起来后悔。
苏茵眼中泛起叹息般的涟漪,像是一声没有说出口的珍重,悄然也给这段不该存在的过去划上了句号。
她正要转身离去,听到柳不言哑着声音唤了一声“苏茵”,像是一方砚台四分五裂。
苏茵侧过头,看着柳不言颓然地半跪在柳家的院子里,头顶着连绵的屋檐,身上淋了些雨丝,衣袍和怀中的红衣都揉皱了。
曾经清亮澄澈的双眼里满是浑浊的红色血丝,像是从天上落到污泥里,沾染了种种的不甘和无力。
就那么含着淡淡的泪光,看着她。
此生的情窦初开,只此一次的荒唐大胆,让他生出许多种不甘来,但他也只能喊出这么一句苏茵,无法说出更多来,没资格挽留,也没法说服自己。
苏茵敛眉,看着他,叹了口气,“郎君若是真的不想要这门亲事,便该去找那新嫁娘说清楚,承担起责任来,该要如何便去做,去宗家赔礼,遣散宾客,柳家一意孤行,郎君既然是柳家的人,便该担起这责任来的。”
“倘若郎君豁不出去这份脸,便认命罢,把那些妄想收了弃了,依照家人所期望的那般,结婚生子,按部就班,不要再想其他的了。”
柳不言保持着仰头看苏茵的模样,视线却被一片泪光模糊,“娘子是这般想的吗?”
苏茵垂眸,“是。这桩婚事成与毁皆在郎君一念之间,不论成与毁,郎君都应该面对,心怀不忿而无所作为,不过徒增怨愤伤悲罢了,无济于事。”
柳不言猛然弯下腰来,强撑的那一口气散掉,没了抗争,也没了心气,“娘子希望我如何呢?”
苏茵却不直接答:“这不该问我,郎君应该问自己才是。你要千夫所指一时自由,还是成全孝道顺应当下,你想要什么,要面对什么,只有郎君自己知道。茵非郎君,无法知晓郎君真正所想所要,自然也没法替郎君做决定。”
柳不言垂着眼,细密的雨丝落在他的眼睫,积攒成硕大的水珠,然后蓦地滴落下来,模糊了他的视线,在这一片模糊中,他瞧见苏茵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只留给他一句珍重。
他坐在院子里许久,终究没有迈过那扇大开的,窄窄的侧门。
苏茵事先从一些安插进来的丫鬟身上摘了腰牌,凭着这个,畅通无阻地出了长安城,绕了段路,去往旁边一座小城上的码头。
苏茵的父母带着若水在码头上等候已久,若水脸上沾了灰,戴着顶草帽,蹲在岸边盯着水里的游鱼。
在她跳下去捞鱼之前,苏茵把她抱了起来。
去往江左的船正好要开了,苏家二老站在船头,才发现苏茵没有上来,依然站在码头上。
“茵娘,你这是何意?”
苏茵擦了擦若水脸上的灰,站在一片夕阳的余晖里答:“不是女儿不想尽孝,只是此间事未了。”
苏茵捂着了若水的耳朵,看向自己的父母,轻声开口道:“我没杀他。”
苏母尚且有些不解,苏父却是脸色一白。
苏茵从袖子里找出一个物件,上前一步,轻轻抛到了苏父怀中,“我在半里之外的林子里遇见了一群持刀的蒙面人,万幸身上带着许多迷药,解决了他们。这便是那些蒙面人身上的东西,父亲,你可识得此物?”
苏父看着手中腰牌上的花纹和刻字,瞬间苍老下来,浑浊的眼睛里倒映着河面的夕阳。
他长叹一口气,骤然佝偻起来,“为父,看错人了。”
苏茵不再说下去,父女一场,有些事情不必撕破了,闹得那么难看。
她父亲这辈子最爱面子,如今看清楚了便是最好,倘若追问下去,反而不好收场。
苏母看这光景隐约明白估计是什么涉及朝堂的事情,也不问,只是走到甲板上,“茵娘,船要开了,有什么事情,你上来不好吗,难不成你要带着个孩子在外漂泊吗?这怎么能行。”
苏茵仰头看着面前的船只,白色的巨帆在夕阳下呈现一种极为漂亮的金色,被风吹的鼓起来。船夫光着臂膀,拉着绳索,喊着号子,河滩边上的鸟展翅而起。
眼前的景象实在迷人,父母眼中的关切也是真心实意。
苏茵微笑着,夕阳落在她眼里,像是温暖的烛火一般。
她往后退了一步,向父母告别。
“我和他的事情尚未了结,他恐怕不会善罢甘休。茵不想给父亲母亲招来灾祸,所以请恕茵不能同去。父亲母亲请放心,茵会保重,每月寄信告知近况。”
“此去路远,还请父亲母亲多保重身体。”
苏母猛地睁大了眼睛,还想说些什么,声音被船夫喊的号子盖过,苏茵只看见母亲满是不解满是不舍的面容。
苏茵立在岸边,抱着若水,就那么看着船只入了水,离岸而去。
她并不怀疑父母对自己的爱,只是她清楚,那份爱混杂在他们脑中的陈规里。
所以他们会替她筹谋,会寻人救她,也会蒙蔽她的过去,将她许了夫家,劝她诞下子嗣,稳固夫妻关系。
真挚的爱和根深蒂固的观念掺杂在一起,就像变质的酥酪一般,一口下去,甜和苦混在一起,无法分开。
她无法靠着这点零星x的爱意和关怀而活着,但却又真真切切会在宅院里凋零。
踏上这艘船只之后,一旦靠岸,不过是那半年宅院生活的反复上演罢了。
苏茵做事,从来都是去想最坏的打算。
再去嫁一个不熟悉的男人,坐在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里侍奉姑婆,生儿育女。
她是宁死也不肯的。
眼见着船只离岸越来越远,苏父苏母站在船边,瞧着苏茵挥手跟他们道别,却始终不肯松口,连一句不日便归家的话也不肯说,重重叹了口气。
“安泽县,槐柳巷。”隔着滔滔江水,在离别之际,苏父开了口,“一年前我们在那里找到的你,你想问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找到你时,若水已经两岁有余,你身边未见什么男子,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她的生父是谁。”
随后一阵滔滔江水声,船只朝着地平线而去,苏茵福了福身,朝父母做最后的告别。
随即将若水放下了,牵着她往最近的一家客栈去,从袖子里掏出一册地图,开始看安泽县要怎么去。
若水倒也不闹,只是一直往旁边看,看到附近有人就睁大了眼睛。
到了客栈,她还坐在床沿上,脆声问苏茵:“燕大侯爷什么时候来找我们啊?”
苏茵正对着烛火找安泽县,听见若水这称呼,眉头一跳,“你叫他什么?”
若水从苏茵的语气中预感到有些不对,但又不知道是为什么,乖乖坐好了,回答:“娘亲不是说不许我叫他爹爹吗,只能叫他侯爷。”
若水声音越说越低,低着头,不时抬眼看苏茵的脸色,鬼灵精的模样让苏茵恍惚间想到长安城里那人。
这个大小不分的称呼谁教的呢。
必然是他教的了。
那自己说过的那些话,若水必然也全漏给他了。
苏茵都能想到那副场景,点着灯的夜晚,她在屋中熟睡,若水和燕游悄悄躲在院子里吃糖,若水跟个小仓鼠一样往嘴里塞,一边塞一边漏些话出来,燕游便蹲在若水身边像个狐狸一样笑,教着她怎么应付苏茵,做他的小细作。
事情已经发生,苏茵也不想追究些什么,只是有些好奇,“他拿什么让你听话的,只是糖吗?从前也没见过你这般。”
若水揪着手,小短腿在空中晃荡,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低到听不见,“燕大侯爷说,我以后就是侯府唯一的小主子,不会有其他的小主子。”
苏茵愣了一下,看着若水,未曾想过她也会有这种担忧。
随即她又想到,从前在江陵,那么多人劝她再生一个孩子,必然也有碎嘴子的在若水面前说过。
苏茵心上浮起一阵歉疚来,正要走过去安慰她,跟她保证不会有其他的孩子,又听若水开口道:“他还说以后等娘亲身体养好了,我长大了,他就把侯府给我,以后就是我说了算,全长安的糖果铺子,只要我喜欢,都能买下来,没人敢不答应。”
话语里满是十成十的雀跃和欣喜。
苏茵看了一眼若水攥成拳头的小手,不知该说她志得意满还是狐假虎威。
苏茵深呼吸一口气,过去拍了拍她的脑袋,打碎了她的幻想,“那你是没机会了。侯府以后我们不回去了,他你也不会再见了。以后就只有我给你买糖葫芦了,七天只能吃一串。”
若水眼中含泪,苏茵侧过头,无动于衷,“我不会改变主意,哭哭也不可以。”
若水顿时就不哭了,瘪着一张嘴,自己躺好了盖上被子,转过身去,只留一个虽然小但敦实的背影给苏茵。
苏茵看着,不禁想到自己从前喂过的猫,平时也看不出来胖瘦,只觉得小小一团十分可爱,到了它压垮藤篮,坐下来变成一个大鸡腿子的时候,才发现它体型似乎有些壮硕了。
要不要干涉呢。
苏茵坐在油灯下想了想。
她才三岁多,正是贪吃好玩的时候,本来日子里盼头就是那点蜜糖糕点,要是这都不许,对一个孩子来说,委实太过残忍了。
她对若水的期待就是平安健康的长大,开开心心的。
算了,爱吃些没什么,健康就行,大不了以后哄着她多运动些。
她又不盼着若水按照当下的美人模样去长去赢虚名。
反正她看自己的孩子,怎么都是可爱的。
她也不盼着若水出嫁。
若是可以,苏茵倒希望若水就一直留在自己身边,不要出嫁,不要去到另外一方宅院里,在她身边,一辈子做个小皮猴也不错。
倘若她长大了少女情窦初开,喜欢上哪家的少年郎,牵扯一番,伤了心便回家,苏茵是愿意照看她一辈子的。
想到以后,苏茵起身,给若水掖了掖被子,坐在床边,谋划着,要是这样,她得选个地方定下来,安家落户,积攒家业,还得能守住家业,这样才能在乱世站稳脚跟,给若水当靠山。
这地方不能太大,不然势力盘根错节,她一人恐怕难以立足,也不能太小,不然也发展不出什么来,还得民风淳朴不能排外。
她想了一些地方,最后看着地图,决定还是先去安泽县看看,看看自己的过去。
安泽县地处江南,四方通达,也是个富庶之地,有不少人家找婿入赘,或者女子自梳。
为了安全,苏茵跟着一队行镖的人,谎称是遭了负心汉,生下幼女孤苦无依,特地前去寻夫。
镖师听了骂骂咧咧,当即拍了拍胸脯,表示这事包在身上。
唯有若水抬着头看着苏茵,眼睛里闪烁着不赞同:明明是你不要他的呀!怎么能说谎!他醒了要一个人躺着哭的!
苏茵忍不住啧了一声,抬手捂住了若水的眼睛。
这孩子,都快姓燕了。
苏茵无视了若水瘪着的嘴角,继续和镖师攀谈起来,一路走,一路从镖师口中得知了不少事情。
比如金陵换了三个长史,先是长安口音,后面又是河南口音,新上任的那个又是江浙人,现在去金陵的行商,身上至少准备四五个地方的东西,免得还没有到金陵,长史又换了一个。
各地的匪患频出不止,现如今偏远地方住在城里的人倒是少数,理由也简单,绿林山匪不用上交重税,这么些年年年新官上任收一波税,寻常人家屋子里的东西,早就掏空了。
那些地方的官兵倒是也不怎么管,固定时间盔甲也不穿,出门“剿匪”,象征性到山下骂两句就草草了事。
据镖师所说,那平梁的“绿匪”中有一个家世凄惨的下雨天横死了,还是官府那几个衙役凑了钱,买了张草席给他下葬。
“可怜哦。”年长的镖师吸了口烟,将烟杆在马车上敲了敲,看着面前的天叹了口气,“这鬼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先是跟胡人打仗,胡人打完了,自己人又打,没消停的了。”
苏茵听着这话摸了摸包裹里的盒子,也叹了口气,她好不容易变卖出的巨款,如今竟也不知道给谁了。
天地茫茫,放眼望去,又有什么人是真的可信,真的一丝党争也不沾,面对这笔巨款也不会变节。
苏茵想了许久,看着荒芜的田地,郊外低矮的谷堆,决定还是自己来。
正好之前各方势力都想利用她,给了不少东西和信物,以及书信。
苏茵拿着这些研究许久,借用了路边写字先生的摊位,仿着长安城里那些个贵人的口吻,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书信,用萝卜刻了印章,印上各种家徽式样,让他们争斗起来,力求把还在赴任准备捞油水的那些人给拦了,使那些个地方县令之位暂且空缺,而后又捏了个富商的身份,借着十七皇子的远亲背景,去救济赈灾。
至于为什么是十七皇子,大抵是因为苏茵在侯府的时候,那么多将相王侯都是派丫鬟来给她递话,半是威胁半是命令她。
唯独八岁的十七皇子站在府门前怯怯看着她,喊了她一声“小表嫂。”
至于身有残疾的八岁小孩为什么出现在府门前,又为什么能刚刚好在她午睡醒来之时正好说出那句话,瘦弱得不成样子了,手里还拿着一个木头玩具说是给若水的礼物。
苏茵并不想去深究。
反正皇家之中都是算计,她宁可选一个有礼貌会装模作样的。
做完这件事情,她反正也不会再掺合,就当是那个木头玩具的回礼好了。
既然他想争,她便给他一个机会,将他推到台前,至x于他背后的人能不能争得过台前的虎狼,那便听天由命。
搅乱朝野的信件就在苏茵饮酒赏月的间隙被装进了信封,盖上以假乱真的印章,夹杂在最简单不过的白纸信封中,沾染着酒气烟气,混在花篮菜篮和酒壶中,送进了各家朱门中。
倘若它是一封装裱精美的信,或者一封纹饰繁复的奏折,管事或许都不会收。
偏偏它经过几重的伪饰,手法十分眼熟,管事不得不信,将它从那些个不起眼的杂物中抽出来,珍而重之地放在了主人家的书房长案上。
长安本就混乱的局势在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弄之下彻底乱成一团。
唯有燕游和徐然嗅到了其中的气息,对视一眼。
“一定是她。”燕游万分肯定。
徐然也不反驳,伸了伸懒腰,“恭喜,你现在可以去找她了,我可以睡个好觉了,别来烦我了。每天被你拉着喝闷酒,我也很郁闷的。”
徐然话没说完,燕游已经翻身上马了,只留给他一抹尘烟。
半个月后,江南百姓得到抚恤的银钱吃上东西之后,苏茵也到了安泽县。
夹在大山和大河之间的一个县城,天险庇佑,因着地处中原,气候也不错,四季分明。
苏茵到的时候已经是夏末初秋,太阳照在身上不怎么晒人,地上的石板泛着一种模糊的白。
她牵着若水进门,不自觉摘了幕篱。
街边卖云吞的大娘抬头见她,笑着念了一声:“苏娘子,你可算回来了,你家中都长满杂草了。”
苏茵一时怔愣,松开了牵着若水的手。
若水把头上的帽子摘了,小跑过去,一点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来,喊了声:“王大娘!”
颇有些向熟人撒娇的意味。
卖云吞的大娘连忙答应了一声,从灶台下面拿出东西开始煮,“嗳!红豆小圆子给你备着呢!你干什么去了,脸脏兮兮的,快擦擦。”
若水擦着脸没有回答,事情太多,她也说不过来。
苏茵看着这座城市,看着这奇怪的建筑,四四方方向天而去的长方形,奇怪的白色道路,以及从学堂里鱼贯而出的少女们。
她们背着书袋,瞧见苏茵,道了一声:“夫子!你回来了!”
一切像是走马灯一般,在苏茵面前快速而静默地闪过,热情的少女们,招呼她的店铺主人,穿着一身浅灰色官袍明显是女扮男装的县令。
最后她来到了位于槐柳巷的荒芜小院,它其实还算干净整洁,只是院子里的花谢了,看起来缺了些生气。
“自你走后,这些花我也时常派人照料,不知道为什么,再也没开过。”县令摘下帽子,揉了揉脑袋,“苏茵,你可算回来了,都没人帮我处理公文了,那些个老狐狸太麻烦了,你伤好了吗?”
苏茵“嗯”了一声,县令见她并未多说,也不多做打扰,“那你先休整一下,我不叨扰你了,我还有许多文书要写,这些个大官一天天变来变去的,都快烦死了。”
苏茵缓慢推开了籓篱,看着自己曾经亲手布置的家,和远在长安的侯府花园差不多,只是没那么奢华。
她往里走,走过书房,花厅,卧房,那种怪异的熟悉感越发强烈,一种似曾相识,但这些布置格局和侯府太像,以至于她有些混淆。
一时间是许多碎片,一时间是她在侯府的时光,混在一起,纠缠着。
她站在日光之下,站在这偏远小城中,仿佛看见千里之外那人的目光,缓慢地落下来,带着悲痛和遗憾以及不甘。
“我曾与你春风一度。”
美人塌下放着一本随笔,苏茵并没有去翻开,把院子收拾好了,等若水睡下来,孤身提着灯,出门,坐在河岸边的石头上,借着月色,翻开书页。
【不知他可好,愿他安好。】
【若水总是问她父亲在哪里,可我不能告诉她在长安,在侯府里。他不会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我只是想要一个与所爱之人的孩子,一个这样的羁绊,和他没有关系,也不必有关系。】
【往事种种,夜深忽梦,醒来泪阑干,我想,我们都回不去从前。】
【我也不知道在这里是在惩罚自己还是他,还是说,山河飘摇,故人长绝,此等情景之下,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在一起。】
【从前我不懂桃花扇,如今我似乎懂了。】
泛黄的书页像是雪花一样落在河面上,漂浮着,晕开了字迹。
苏茵坐在岸边许久,看着漆黑河面,像是在看从前,又像是在看晦暗的未来。
直到河面泛起涟漪,她看着万分熟悉的身影踏水而来,像是游过记忆和迷惘,越过从前,从虚无的彼岸游到她的裙边,湿漉漉的指节抓住了她的足踝。
“苏茵。”他仰起头,面上水光映着月色,叫她名字,像是从前千千万万次一般。
“你又抛下我。”他看着苏茵的眼睛里满是委屈和气愤,正要抓着苏茵上岸。
苏茵指尖摁在他肩膀上,止住了他上岸的动作,“好玩吗,这段日子,玩霸道侯爷和小娘子。”
燕游身形一僵,缓慢看向苏茵,目光又逐渐偏移,讪笑一声,“夫人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苏茵把他脸掰过来,“不是很喜欢这样掰我脸吗?还问我想着谁,让我哭喊着叫你名字,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
燕游抿着唇不吭声,连狡辩也放弃了。
苏茵坐在石头上,托着下巴看着他,慢悠悠地开口,“江陵的时候我信你不知道,去了长安,你会不查?你早知道若水是你孩子,也知道我和柳不言婚姻名不副实,非要折腾我,觉得那样很满足?”
燕游站在水中,看着河面,身高八尺的大汉背着手低着头,“我一见面就说了,你不信,还骂我痴心妄想来着。”
“然后你就把我虏了,把不该做的全做了,仗着我什么都想不起来,觉得我想起来了也不会怪你。”
燕游目光往外飘,跟犯了错的若水一个神态,知道自己错了又不想认。
苏茵摁了摁额角,把他往水里一推,撩起衣角往外走,“什么时候知道错了,什么时候再来见我。”
没走出两步,苏茵身后就响起燕游的声音。
“苏茵,你鞋子没穿好!会着凉!”
“不是,你听我解释,那个时候情况比较复杂,那么多人盯着,我怕你受伤。”
“你信我,你信我啊!”
圣堂山上的墓碑长出青草,朝野之上的左相又换了人,长安的斗争还在继续,你方唱罢我登场,漠北的草原也迎来了新的王子,新的王庭。
所有的旧事逐渐被新人所取代,苏茵走过河堤,看见新一轮太阳冉冉升起,草上的露珠泛着白光。
那熟悉的声音还在身后喋喋不休,热闹地占据着她的从前,当下,以及不知多漫长的未来。
“造成圣堂山惨案的那些人你以前都认识,我不是怕你难受吗,所以才一个人把他们宰了。”
“不是不让你参加,他们都是混蛋,不想脏了你的手。”
“苏茵,别生气了,苏茵。你想对付的那几个蛀虫,我来路上帮你都宰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告诉我一声,我替你去做,何必那么麻烦。”
“苏茵,苏茵,理理我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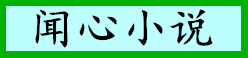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