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不徐不疾道:“自然。何时他想明白了, 自然能出来了。朕是要让他明白,他是储君,怎能事事都顺着他的心意。”
他以为许知意会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明白了, 尔后赶忙回宫告诉顾晏辞此事。谁知许知意也不知是受了何等刺激,竟然在沉默片刻后道:“既然陛下心意已决,那儿臣只好回去同太子殿下一起禁足了。”
他旋即蹙眉, “你说什么?”
她洒脱道:“陛下不是说若是儿臣不将此事告诉殿下, 殿下便要一直被禁足吗?儿臣想了想,太子殿下就算知晓了此事, 应当还是会选择禁足的, 所以儿臣还是陪着他一起禁足好了。”
天子怒极,冷笑道:“好, 朕瞧他娶了个这般不知礼数的太子妃。既然如此,那你便回东宫,和他好好待着吧,莫要再想着出来了。”
回宫时,许知意让春桃从各家酒楼过了一遍,应季的美味都买了,这才回去。
先前本来她是不必禁足的,这下好了, 自己殷勤了好几日,结果把自己折腾到不得不禁足了。
她想想便恼火,忿忿道:“陛下吃了我那么多东西,竟然还拿纪家三小姐的事情来为难我, 最后居然让我禁足,这实在不是君子所为。”
不过,不就是禁足吗?平日里她本来也出不去, 禁足也没什么好畏惧的。
哼。
顾晏辞一看见许知意的脸色,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一回去便忍不住道:“我今日……”
顾晏辞抬手,“且慢,你让我猜猜。是不是陛下不仅没告诉你何时能放我出去,还拿旁的事情威胁你了?我再猜一猜,兴许是纪家三小姐的事情?”
她愣了愣,“殿下怎么知道的?”
“看你脸色,我不用猜都知晓。”
结果他一转身,看见后头春桃派人往里头搬各类吃食,惊道:“你这是做什么?”
不知道的还以为天下大旱了。
许知意老实地把前因后果都说了。
顾晏辞无奈道:“本来你是不必禁足的,这下倒是好了,自请要同我一起禁足。”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能说不禁足就离开吗?”她哼了声,“反正有这些吃食,我就不怕了,陛下爱关多久关多久好了。”
两个人性子上都有一个相同点,一个是无论如何都处变不惊,一个是一旦认清了目前的情况,便也处变不惊了。
于是两个人就这么慢悠悠在东宫里待下去了。东宫上下见两位主子不急,自然也急不起来了,就这么安安静静地伺候二人。
东宫的门禁闭着,日子却像檐下滴漏的水,不紧不慢地淌过去。起初外头还有些试探的动静,或是几道请安的折子,或是一些拐弯抹角的问候,都被顾晏辞淡淡地挡了回去,递也递不进东宫去。久而久之便真如他所料,除了皇后宫中偶尔送些用度之物,再无其他声响。朝堂之上虽都在揣度天子的心思,但见天子久久没有放太子出来的意思,也不敢多置喙什么了。
食官署的供给依旧简素,好在许尚书心疼女儿,总能设法递进来些实在东西,譬如油纸包着的炙鹅,瓷瓮煨着的汤,甚至还有一小坛醉蟹。顾晏辞见了,只抬抬眼,并不说什么,许知意便当他默许,乐得改善伙食。
她自己买的吃食很快就吃完了。若不是许尚书惦记着她,她觉得自己真的能饿死在东宫。她不由揣测,当初天子下的旨意完全就是针对她的,他知道她贪嘴。
毕竟顾晏辞这个人,无论吃什么都无所谓。虽说这段日子因为这可恶的膳食,他都清减了不少,穿着件月白色银丝暗纹团花长袍,看着像是要羽化登仙一般,但他仍旧什么都没说,也没说要吃许尚书送来的东西。
许知意好心提议让他吃一些,他却也好心提议让她自己吃完,毕竟他是真的怕她不够吃。
许知意因为久久未吃到好吃的膳食,已经面色无光了,一到用午膳时就要哀嚎一番,然后对着顾晏辞道:“殿下,等你出去后,你知道要做什么吧?”
他点头,“我知道,直接把你送进食官署,你要吃什么都让你吃个够。”
许知意只能画梅止渴,画饼充饥。有段日子替许尚书递送吃食进来的梁瓒病了,于是也没有可靠的人可以递送吃食进来,便停了一段日子。
这下好了,许知意撑了七八日,终于忍不住在凝芳殿对着春桃和见夏哀嚎道:“我活不下去了。”
本来她只是抱怨一番,结果被长乐听见了,传过去的话便变成了:太子妃在凝芳殿寻死觅活。
他大惊失色地冲进崇明殿,以为顾晏辞会和他一样大惊失色,谁知他压根没有。
他反而对于许知意忍耐到现在才寻死觅活很惊诧,不用问都知道她是为了什么,于是淡淡道:“去问问梁舍人身子好转了没有。”
长乐去问了,回来道:“殿下,梁舍人说他卧病在床,无法起身。”
“无法起身也让他起来。卧床七八日了,若不是腿折了,本宫想不明白他为何起不来。”
长乐又跑过去转告了,回来道:“殿下,梁舍人还是说他无法起身,虽然没有腿折,但一起身便呕血不止。”
顾晏辞轻嗤一声,“告诉他,他若是能起身,赏银千两。”
长乐果然回来道:“梁舍人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虽病矣,但也能为殿下效力。只是呕血,也不打紧的,有什么事,他边呕血也能做完。”
尔后许知意就收到了许尚书递进来的各类吃食。
她有些困惑道:“梁舍人不是还病着吗?怎么今日忽然好了?”
但无论如何,她至少吃到了自己想吃的。
由于这段日子在东宫里实在格外无趣,许知意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最后她觉得自己即将失智,于是问长乐,宫里的娘娘平日里都如何消遣,长乐答,可以养些花草或者畜玩。
最后她养了只鹦哥。但由于雪团不大喜欢这只长相奇异的奇物,而且它太过吵闹,许知意逐渐失去了耐心。旁人的鹦哥都是能学人言,巧舌如簧,她养的这只不是,许知意让她学自己说话时它一言不发,但等她走近时,它便冷不防扯着嗓子大叫。
最后不仅是许知意忍不了了,凝芳殿里的所有人都忍不了了,她很认真严肃地对着它道:“你若是再这样下去,他们说不定会在某日夜里把你杀掉,到时候我也保不了你,明白了吗?”
它用更加凄厉的叫声表示自己听不明白。
呕哑嘲哳难为听,许知意百思不得其解道:“它怎么会这样?”
顾晏辞凉凉道:“有其母必有其子。”
许知意气急败坏道:“跟我有何关系?我看雪团不就很好吗?”
顾晏辞勾唇笑道:“因为它更喜欢我啊,你难道没发现么?”
正说着,雪团已经轻车熟路地跳上他的腿,他修长的手指抚了抚它的脑袋,它则格外谄媚地在他的怀里蹭了蹭。
许知意一摊手,“好啊,那我把它交给殿下,看殿下能把它调教成何种模样。”
没几日,顾晏辞邀请她去崇明殿看鹦哥,她这才发现它居然已经学会了读诵诗词了,而且看见她时也会唤“许棠棠”,而不是呕哑嘲哳难为听的大叫。
许知意甘拜下风,决定侍弄花草。
她一边修剪花枝一边喃喃自语道:“何时能开花我们何时便能出去了。”
顾晏辞好心道:“你还是莫要养了,到时候花草短命,兆头不好。”
她心想,你怎么知道我会养死呢。
最后的最后,五日后,她捧着一盆花,格外谄媚地去了崇明殿,询问顾晏辞有没有什么好法子救活它。
这日晌后,难得的晴暖,许知意正指挥着春桃,将她那几盆半死不活的花草搬到廊下晒太阳,长乐却进来通报,面上带着些许为难,“殿下,太子妃,纪太傅府上的三小姐来了,说是奉了陛下的旨意,来给太子妃送些时新的花样子,并……探望殿下。”
许知意擦手的手一顿,下意识看向坐在窗边看书的顾晏辞。
皇后娘娘都不能亲自来看他们,结果天子却派了纪家三小姐来。
这分明就是故意的。
虽说她还挺喜欢纪家三小姐的,但是她此刻不想看见任何能自由进出的人。
他目光仍落在书页上,神色未动,只问了句:“只她一人?”
“是,只带了两个侍女,提着些礼盒。”
顾晏辞合上书卷,淡淡道:“既是奉了爹爹的旨意,便请进来吧。于礼,也该谢过爹爹记挂。”
不多时,环佩轻响,一位身着浅碧色春衫的小娘子款步而入。身量纤秾合度,面容清丽,行动间仪态娴雅,确是好教养的闺秀模样。她先向顾晏辞行了大礼,“臣女拜见太子殿下,殿下万福。”
她起身,又向许知意行礼:“见过太子妃殿下。”
“这是家母新得的一些苏绣花样,想着宫中或也新奇,特让臣女送来给殿下赏玩。另有些自家制的杏仁酥、茯苓饼,聊表心意。”
许知意让春桃接下,笑道,“难为三小姐还特意跑一趟。快请坐,春桃,上茶。”
许知意从第一次见到她就很喜欢她,她觉得她和许知泠很像,是真正的名门闺秀,有种吸引人的特质。于是她就算讨厌一切可以自由出入的人,但也还是忍不住拉住她的手道:“如今东宫里没什么好吃的膳食,你且将就一下。不如你陪我一同去玩双陆吧?”
虽说她技艺很差,但她明显迁就了她,于是许知意也能偶尔赢上一两局。
本来应当是进宫探望顾晏辞,但硬生生变成了许知意和她的手帕之交,顾晏辞倒是巴不得两人交好,自己也能不掺和进去。
不过许知意似乎能和大部分女子处得好,这倒也是个本事。
最后两人又去玩投壶。许知意投得乱七八糟,自己却也不觉得丢脸,纪家三小姐投得却格外漂亮,她毫不在意,反而凑过去,盯着她道:“你真的好厉害呀,什么都做得很好哎。”
她垂眸,微微笑了,“太子妃过奖了。今日我来,其实也只是因为陛下的旨意,陛下一心想让我进东宫,但我既然先前已经答应过殿下,便不会再打这样的主意了。今日能进宫陪着太子妃便很好,也希望太子殿下莫要觉得我是故意进东宫来打搅他的。”
许知意一连声道:“不会的不会的。”
两人又待了一阵,她这才从东宫离开。
最后许知意感慨道:“没人会想要让此事成真,陛下就不能为我们三人考虑一番吗?非要如此固执,真是让人头疼。还是纪家三小姐好,她还给我带了糕点呢,我真是喜欢她。”
这样她又能撑一阵了。
又过了些时日,许尚书的书信,随着一匣子新腌的醉蟹送到了许知意手中。信上并无特别紧要之事,只絮絮叨叨说了些家中近况,末尾却笔锋一转,“……宫中近日风波不断,爹爹远在宫外,听闻种种,心实难安。吾儿性情率真,东宫如今处境微妙,万事需得谨慎,尤要保全自身。若真有难处,许家永远是吾儿后盾,纵使万难,为父亦当竭力。”
晚间,许知意将信给顾晏辞看了,指着最后那段:“我爹爹是不是担心过头了?”
顾晏辞看完,眸色深了深,将信纸折好还给她,“许尚书是明白人,也是真心疼你罢了,自然会担忧。”
许知意托着腮,忽然叹了口气:“爹爹也真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都是太子妃了,难道还能……”
她顿了顿,眼珠一转,不知想到什么,自顾自嘀咕起来,“再说了,就算真有什么万一,现下改嫁也来不及了呀。后头那几个皇子,五皇子看着就不太聪明,六皇子、七皇子年纪比我还小呢……”
话未说完,便觉一道目光落在了自己脸上。她抬头,正对上顾晏辞的眼眸。他不知何时已放下了手中的笔,正静静看着她,脸上没什么神情,但却让她心里莫名一虚。
顾晏辞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太子妃连后路都筹划得如此周全了?连几位皇弟的年齿,都记得这般清楚。”
许知意脸上忙摆手,“不是不是,我就是随口一说。”
顾晏辞却已经放下了笔。他没起身,也没走近,只是抬起眼,静静地看着她。目光清淡平和,甚至没什么额外的情绪,好似看她和看砚台没什么区别。
然后许知意就莫名心虚了,莫名底气不足地低头道:“我就是想要改嫁,他们也不要我呀。而且我方才就是胡说的,殿下不会当真的吧?”
顾晏辞依旧没说话,尔后站起身。许知意吓了一跳,以为他要斥责或是说些什么,却见他只是绕过书案,朝自己走了过来。步伐不疾不徐,衣袂微动。
她下意识地想往后缩,后腰却抵在了桌上。顾晏辞在她面前站定,两人距离不过咫尺。他身上那股熟悉的、带着墨香与淡淡冷意的合香笼罩下来。
他还是没说话,只是伸出手,不是握她手腕,而是直接捏住了她的后颈。力道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意味。
许知意仰起头,懵懵地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烛光在他挺直的鼻梁一侧投下淡淡的影。尔后,他低下头,毫无预兆地吻住了她犹在微微张合、试图继续辩解些什么的唇。
她彻底僵住了,唇上传来温凉而柔软的触感,她瞪大眼,能清晰地看见他低垂的睫羽。他的吻起初带着些微的力道,似是惩罚她方才的口不择言,随即渐渐放缓,却并未离开,只是辗转厮磨,温热的气息与她急促的呼吸交织在一起。
顾晏辞看着她的模样,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几不可察的、近乎餍足的暗色。但他脸上依旧没什么多余的神情,只是用指腹很轻地擦过她湿润的下唇边缘,动作自然得仿佛只是拂去砚台上的一点尘埃。
他开口,声音比平时低哑了些,“去给许尚书写回信吧。好好写,让他莫要担忧。”
许知意晕晕乎乎地下意识点了点头。
他这才彻底松开她,转身,重新走回书案后坐下,仿佛方才的一切从未发生。
又过了半月,顾晏辞始终淡然,依旧看书、习字、与许知意对弈,偶尔指点她那并无长进的棋艺,或是听她兴致勃勃地讲述她那几盆花草(依然半死不活)的“长势”,又或是她不知从哪里听来的、离奇的宫闱传闻。
许知意已经逐渐习惯,只是偶尔才忿忿道:“我看陛下还准备把我们关多久,实在毫无人性嘛。”
朝堂上本来对天子禁足太子一事颇有微词,但后来也不得不揣测圣意,是否是想要废储君另立,于是一时也无人敢再提起此事。
许尚书递消息进来时也在信中表达担心,不知两人到底何时才能出来。他甚至在外偷偷带着许家人求神拜佛,只为求让二人出来。
就在许知意彻底绝望之时,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暮春的倒春寒来得又急又猛,料峭的风裹着湿冷,一夜之间摧折了宫中不少初绽的花苞。天子本就未愈的旧疾,在这骤寒侵袭下,陡然沉重。
起初只是风寒加剧,继而转为高热不退,汤药难进,直至咳中见红。太医院诸位御医轮番值守,脉案方子换了几轮,龙榻前药气日夜不散,那沉疴却未见起色,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宫墙之内,消息纵然竭力封锁,那股山雨欲来的压抑,依旧顺着门缝窗隙,由宫人的口舌传递,悄然弥漫开来。
这一日,午后天色便昏沉得异样,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宫阙飞檐,无风,却有种窒闷的静。顾晏辞正在书案前临帖,许知意在旁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琐事。殿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是长乐。
他几乎是跌撞着进来的,身后还跟着梁瓒,脸色在昏暗光线下白得惊人,额角尽是细汗,声音压得极低,却止不住地发颤,“殿下,大庆殿传来消息,陛下病情危急,皇后娘娘、几位阁老都已跪在殿外,陛下说他要见您,让殿下速速过去。”
顾晏辞手中的笔,正写到“永”字的最后一捺。闻言,笔尖在宣纸上微微一滞,墨色随之凝住,旋即迅速洇开一小团,将那即将收尾的工整笔划,晕染得面目全非。他垂眸,看着那团碍眼的墨渍,静默了一息。
他搁下了笔,动作平稳,不见慌乱。目光从污了的字帖上移开,转向长乐,声音听不出什么波澜,只比平日更沉静些,“知道了,替本宫更衣。”
宫人早已捧着正式的冠服候在一旁。许知意站在旁边,看着他由人服侍着更换衣物,系上玉带,戴上金冠。整个过程,他神色平静,甚至未发一言。她犹豫片刻,最后在他准备出宫时也未说出什么话来。
毕竟谁都知道,这个时候让他进宫,是福还是祸,谁也说不清了。
反倒是顾晏辞知道她想说什么,走到她面前,“莫要担心什么,先前我答应过你的话是真的,你在东宫待着便好。”
许知意低着头,“噢”了声。
他却对着长乐道:“你莫要跟着我进宫了,既然东宫已经开了门,那你便出宫给太子妃买些她要吃的糕点进来。”
长乐也不敢进宫面对这等情况,听了这话,连忙点头道:“是。奴婢这便出宫。”
踏入大庆殿,浓重得化不开的药味混合着一种沉沉的、属于生命即将流逝的衰败气息扑面而来。殿内光线昏暗,只燃着几盏宫灯,将人影拉得晃动而模糊。御榻前,太医和内侍跪了一地,屏息凝神,唯闻天子粗重艰难的喘息,如同破旧的风囊。
顾晏辞撩袍,在离御榻十步之遥处跪下,“儿臣拜见陛下。”
榻上的天子似乎挣扎了一下,挥了挥手,声音嘶哑微弱,“都……退下。”
宫人如蒙大赦,悄无声息地迅速退去,只留下内侍在门口垂手侍立,将最后一丝天光隔绝在厚重的殿门之外。
殿内陷入一片死寂,只有那喘息声,一声重过一声,敲在人心上。
天子的声音气若游丝般落在地上,滚了几圈,“近……前来。”
顾晏辞起身,一步步走近。龙榻上,那个曾经掌握生杀予夺令朝野震动的君王,此刻形销骨立,面色灰败如金纸,眼窝深陷,浑浊的目光费力地聚焦在他脸上。不过数月,竟已憔悴至此。
父子二人,一个立于榻前,一个卧于病榻,隔着咫尺之遥,沉默地对视着。
良久,天子才艰难地开口,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挤压出来,“朕的身子,怕是不成了。”
顾晏辞垂眸,话说得敷衍,“爹爹保重龙体。”
“保重……”天子扯动嘴角,似想笑,却只发出一声短促的气音,带着无尽的嘲讽与疲惫,“这副身子朕自己清楚。今日叫你过来,是有话要交代。”
他停住,喘息片刻,眼珠转向顾晏辞,“你是储君,怕是恨不得这一刻早些来吧?这江山,这副担子,终究要落到你肩上。正好你三皇兄也去了,无人可以再阻挡你。”
顾晏辞静立不语,玄色的袍服在昏暗灯下几乎与阴影融为一体。他本心生怜悯,听了这话却不由得厌烦起来,明明是要将此事托付给他,却又提起了已去了的人。
似乎死了的人都比他更有分量。
“你心里……定然恨朕。”天子的声音更低了些,却字字清晰。
他依旧敷衍开口,“儿臣不敢。”
“是不敢,还是……不愿说?”天子的目光紧紧锁着他,“自你幼时,朕便对你严苛至斯,甚少给予温情。对你三皇兄,却多有纵容宽宥,你心中定有怨怼。”
这倒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顾晏辞的视线落在龙榻边缘繁复的龙纹上,懒得接话,殿内只余天子吃力的喘息。
“储君之位,非同儿戏。”天子自顾自地说下去,“玉不琢,不成器。真正的储君,当经千般锻砺,历世情冷暖,洞人心权术,更要……心志似铁,能忍常人所不能忍。”
他闭了闭眼,“所以,朕对你严苛,是想看看你能承受到何种地步。对你三皇兄,是朕私心,是朕溺爱。以为总能护他周全,可到头来,是朕害了他。”
顾晏辞听着,面上依旧没有什么神情,只是淡淡地看着他道:“爹爹用心良苦,儿臣感激不尽。”
天子似乎并不在意他这近乎敷衍的回应,费力地喘了几口气道:“朝政……内阁诸臣,堪用。五郎,心性能力,皆不足。朕已拟旨,令其就藩蜀地,无诏,永世不得回京。”
“儿臣明白。”
“后宫……皇后会助你。纪氏之事,朕不再逼你。但东宫子嗣,关乎国本,你心中有数。”
“是。”
“去吧……让皇后进来。”
他极其轻微地挥了挥手,阖上眼,不再言语。
顾晏辞对着龙榻,深深一揖。尔后转身,稳步走向紧闭的殿门。内侍无声地打开门,残阳最后的余晖斜射进来,血色笼罩着他的衣衫。
走出大庆殿,暮色已沉。
顾晏辞踏出大庆殿时,最后一丝天光正从飞檐尽头褪去。暮色四合,宫灯初上,寒浸浸的风扫过空旷的丹墀。
他没有理会阶下静候的步辇,独自走下漫长的汉白玉阶。
譬如他曾无数次想要拿着剑对着天子刺过去,但今日刺了才知晓,外头是恨,里头却是怜悯。
这样想来,世间万物似乎也并没有什么意义。
阶底广场开阔,他一眼便看见了东宫那辆青篷马车,以及车旁那抹素色的身影。
许知意披着件月白的披风,立在车辕边,正望着他来的方向。宫灯暖黄的光晕笼着她半边身子,在渐浓的夜色里,像一株安静绽放的晚香玉。
他朝她走去。
她也看见了他,没有迎上来,也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等着。待他走到近前,两人这才四目相对。
许知意到底是在东宫待不住,说什么也要亲自来一趟。看到此人好歹走出来了,这才松了口气。
顾晏辞没说什么,只是对着她伸手,盯着她,一切如常道:“走吧。”——
作者有话说:不想写后续天子驾崩等具体内容,因为感觉对于男主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还是小甜文风格比较好。
所以正文内容大概就到这里,后面会接着更后记和番外,主要是女主真正成了中宫后的后续小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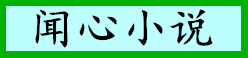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