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远处, 骏马高嘶着刹住,长嬴跨在马上,面无表情地放下大弓, 细看,眼底却腥红, 手指不住地颤抖。
燕堂春被燕衔之的血泼了满脸。
而燕衔之顶着一双充满惊异与不甘的眼睛永远地倒在了地上, 手里还握着那支没射出去的箭。
燕堂春虚脱地后退两步, 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燕衔之的尸体……还温热的尸体。
她忽然就落下泪来。
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燕堂春就通通不在乎了, 她执拗地盯着燕衔之的尸身, 这具尸体被赶来的人收殓后才离开她模糊的的视线。
她被长嬴带到同一匹马上,又一次被长嬴扔到公主府的房中。
一切都和前几天一模一样。
不一样的是,这一次锁住她的不是披帛, 而是锁链。
锁链一头连接着燕堂春的手腕, 一头扣在床头上, 长嬴抵着燕堂春的额头, 眼皮都没动一下, 就着这个姿势说:“着凉了?”
燕堂春摇了摇头。
“等会儿让御医给你看看。”长嬴轻轻地说,“你也不必再出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 燕堂春才觉得她们这样的姿势不太对劲,有点像她梦里那两个纠缠的姑娘。
燕堂春张了张嘴, 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却冷不丁地注意到长嬴的眼睛。
漆黑的眼珠里只有燕堂春自己一个倒影, 眼白被红血丝充斥着,眼眶猩红,哪还有半分平日里清冷庄重的模样,任谁见了这双眼睛都得觉得它们属于一个疯子。
但长嬴的神色却极其冷静, 甚至冷静到了漠然的程度。
这样的表姐……有点吓人。
好死不死,手腕上的锁链就在这时动了一下,燕堂春一惊,见是长嬴在试它的硬度。
更可怕了。
这个时候还是别说话了。
于是话到嘴边,又被燕堂春囫囵咽了下去。
长嬴在燕堂春的手腕与锁链隔着到地方垫了块帕子,然后往后退了几步,视线上上下下地在燕堂春身上扫了半天,似乎在思考她还能怎么跑。
燕堂春顺从地把鞋踢飞了,示意自己不跑了。
长嬴轻轻地把头一点,也看不出满意还是不满意,一句话都没再说,转头就走。
门又被锁上了。
不止是门,这回连窗都封了。
燕堂春往后一仰,躺在了柔软的床榻上,只觉空前的疲惫朝自己涌过来。
院子里的东屋被收拾得利落,三间打通,靠里的是小憩的地方,中间是书房,最外面偶尔用来会客。
不过大多数时间长嬴都不用这里,在正屋里就把事情处理了。
今日例外,房间锁了,长嬴便来书房里办公事。
她坐在桌后揉着眉心,好一会儿,眼中的血色才渐渐褪去。
宫里打发人来了三趟,长嬴都没应,只给人塞足了银钱,让人带话说改日入宫。
徐仪进来时,长嬴已经完全恢复过来。
关于这对表姐妹之间的感情,徐仪恐怕比她们本人都清楚。
因此一得知燕堂春偷跑出去做了什么,徐仪当即就知道坏事儿了。果不其然,她家殿下拎着呆愣愣的燕堂春回来了。
徐仪数着时辰等了好一会儿,才掐点进了书房,见长嬴面无异状,先松了口气。
进来后,徐仪权当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往常一般开口,中规中矩地交代道:“宫里人都打发了,陛下倒没说什么,太后的意思是昭王虽被废,却不能被私刑绞杀,希望殿下能就此事给朝中一个交代。”
长嬴嗯了声,把一封奏疏往徐仪的方向一推:“我方才写了写,你看着润色一番,择日送进宫便是。闵氏竟然没有别的反应?”
“太后还惦记着殿下许出去的好处,恐怕不敢和殿下翻脸。”徐仪略笑了下,发现长嬴状态不赖,便试探道,“堂春姑娘她……”
“说到她,”长嬴打断道,“派人那我的对牌去请御医,她估计是吓着了,有些发热。”
徐仪嗳了声,又说:“我问旁的呢。”
长嬴支着下巴说:“谁知道。去请吧。”
长嬴避而不答,徐仪只好当个睁眼瞎,又问:“今晚殿下在这边睡?”
长嬴说:“回房睡。”
御医来得快,得知后,长嬴淡定地表示知道了,并没有要动作的意思。没多一会儿,她又撂下奏疏,把笔放在笔搁上。
跟在徐仪后面出了门。
徐仪正要开锁引着御医进正屋,忽然一回头,和长嬴对视上目光。
徐仪摸不着头脑:“殿下跟来做什么?”想通后,她唇角带笑,眼尾是藏不住的揶揄,调侃道:“原来是不放心榻上的秦罗敷。”
长嬴蹙眉:“少废话,开锁。”
御医进屋后,眼观鼻鼻观心,假装自己是瞎子,看不见那副扣在人家手腕的的锁链,痛快地搭脉诊断完,给开了副安神的药。
“姑娘并没有大碍,只是长期压抑下骤然放松,又受了惊吓,这才发起热来。仔细将养着便是了。”
长嬴点头,徐仪上前给御医塞了个荷包,礼貌地引着御医出门去。
一直到把人送到府前,徐仪又塞了第二个荷包,对御医道:“我家殿下平时没几个玩到一块儿的朋友,燕姑娘算一个,殿下处处护着她。您心里清楚吧?”
御医接过荷包,会意道:“老朽自然不会乱说。”
徐仪客客气气地应声,吩咐车夫把御医送回府上。
房中,燕堂春已经醒了。
但她不太想理人,翻身就要背对着长嬴,结果被锁链一扯,身没翻成,手腕闪了一下。她轻嘶一声,长嬴下意识掀开帐子,快速握住她的手腕,摁了摁,确认没伤到,才松了口气。
帐子里,两个人一躺一弯腰,都有些尴尬。片刻后,长嬴松开她的手腕,退一步坐在床沿,叹了口气。
燕堂春翻身面对着长嬴,说:“对不起,表姐。”
长嬴冷淡地回答:“没什么对不起的,你要死便死,我不再拦你。”
燕堂春笑了:“那你倒松开我。”
长嬴瞬间盯住燕堂春的眼睛,燕堂春笑容渐渐收敛起来,她低声说:“我知道表姐不肯定他死罪是为我好,我对不起你。我就 是……忍不了。”
长嬴:“我有一点想不通。”
燕堂春:“我也是。”
长嬴垂眼看着她:“我先说。”
燕堂春道:“好。”
长嬴:“流放路上有的是人劫杀,你为什么非得自己动手?还用劫人这种大动干戈、作茧自缚的法子?”
“因为我想亲手了结他。”燕堂春弯了弯眼睛,如实回答,“我九岁那年与你一起习武,曾在王府练射箭,却被他一箭钉在头发上,差点就没了命——那时他没想真杀我,只是戏耍罢了。我却发誓,我要用这个法子亲手了结他。”
长嬴哦了声:“所以一见有个机会,你闻着味就凑过去了。”
“对,我一刻都不愿意再等。”燕堂春:“我也有个疑惑,想让你解答。”
帐子里面有些暗,长嬴起身把帐子拢到一起,天光从茜纱窗外投到屋里,又把帐子里熏亮一半。
长嬴开口道:“你问。”
燕堂春看着她拢帐子的动作,想起来梦里消失在帐子里的两个姑娘。她想了想,问道:“表姐对我是什么感情?像对妹妹一样吗?”
长嬴手里握着帐子,绳结只系了一半就又松开。长嬴面色沉着地嗯了声,手里的绳子却始终系不上,越理越乱。
燕堂春凝视着长嬴修长的手指,笑了:“看来不是当妹妹。”
帐子无声散了下来。
“我也是,我不把你当姐姐,哪怕我喊你那么多年‘表姐’。”燕堂春说,“表姐,我不是小孩子了,你何必再因为我年纪小就不理会我的心?”
长嬴站在床边,微微弯腰再次收拢散落在地的银红色的纱,仓促提起其他话头。
“父正则子亦正,他对你如此苛刻,我不怪你杀他,况且那一箭是我的手笔,也怪不到你头上。”长嬴轻声说,“我怪的是你几次三番把性命当做儿戏。堂春,那你不如早早告诉我你向死之心,早知今日,那么过去那些次,我绝不救你,免得如今提心吊胆。”
燕堂春说:“姑姑说你很在乎我。”
长嬴扯了扯嘴角:“我自作孽。”
燕堂春:“别收帐子了,你没发现你收不起来吗?”
一方狭小天地中陡然昏昧了,红帐落下,长嬴来到床边,燕堂春看清楚了她眼底已经藏不住的情绪。
是欲色。
山火般点燃了。
燕堂春笑了笑,左手撑着床边就要坐起来,谁知唇还没凑到长嬴那边,她就被长嬴反手按回床榻上。
长嬴低睨着燕堂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枷锁会捆死我们。”燕堂春晃了晃锁链,在叮叮当当的响声里,她笑着说,“我们一辈子都得听着这链子的声音。”
这态度太坦然了,就好像她根本不在乎万人唾弃的未来、不在乎孤舟一系的处境。
但长嬴不能不在乎。,
她比燕堂春大几岁,身处的位置危险一层,她不能不考虑那些问题。
可她数次试图开口说些什么,到了喉咙的话却都说不出来,最后燕堂春反握住长嬴的手,再次仰身去碰她。
碰到了。
面颊相贴的瞬间,燕堂春想,真好。
这是一个情意并不明显的吻。
几息后,长嬴深吸一口气,她推开燕堂春,快步起身离开,她把锁挂在屋内,确保外面没人会进来后,长嬴又回到帐子。
长嬴按住燕堂春,语速很快地说:“我想要的有很多。”
燕堂春默不作声地笑看着她,又凑上去亲了一下,蜻蜓点水似的。
长嬴哑声说:“我贪心不足,野心不止。”
燕堂春:“但我只想要你一个。”
这句话的含义太真挚,真挚到哪怕早有察觉的人也忍不住心颤。
深宫里遇到的烈阳……在手里了。
烛火熄灭,帐子彻底落下来。
…………——
作者有话说:感谢阅读[捂脸偷看]
今天还有两更,我睡醒再写。
第28章 送心
翌日清晨, 长嬴重新锁上燕堂春的手腕,没喊醒人,只替人搭了个被角, 就打开屋门的锁走出去。
等到在东屋收拾完自己,已经是半个时辰后的事情了。
徐仪敲敲门走进来:“闵三小姐递的帖子说今日来拜见, 殿下在哪里见?”
女使们端着水出去了, 长嬴系上腰间压裙的玉佩, 说:“去花厅吧, 免得吵醒堂春。”
“正好花厅外头缸子里的荷花也开得好。”徐仪说完, 仔细瞄了眼长嬴神色, 问,“还锁着呢?”
长嬴:“让人搬缸荷花到这边来……罢了,她也看不到, 你等会儿往屋里添些冰吧。给她把药熬上, 她夜里还是有些烫。”
这话听完, 徐仪就知道这不光还锁着, 恐怕连得寸进尺的机会都没给人家。
她欲言又止半天, 最后觉得自己也不该插嘴人家房中事,还是咽回想说的话, 悄悄退了出去。
花厅外的水缸不大不小,一缸里能有四五朵粉白的荷花, 都是从花园的池子里移进去的。花厅外也不贪多, 只摆了两缸增色。
难怪徐仪特意提起, 这两缸荷花的确好,花瓣柔软娇嫩,而且有新意,荷花旁还移植了荷叶。
花叶交称, 不是一般的漂亮。
长嬴还没走近就能闻到荷香,幽幽暗香格外清远。
而整个花厅里都是清香。
闵恣早在里面等着了。
原本闵家为了禁军,给她订了刘胡叶的亲事,但群贤宴事后长嬴提了连三营的副将何超接管禁军,刘胡叶被调到连三营,闵家仔细考量过后,觉得刘胡叶不再值得嫁女,便退了婚事。
“还在议亲,至于议到哪家……谁说的准,但总归给我拖延了一段时日。”闵恣垂眼盯着茶水在杯中晃荡,很快又抬起眼,对长嬴笑了笑,“还要感谢殿下帮我退刘家婚事。”
闵家要退婚,刘家自然不肯放过这个迎娶世家女的机会,两家纠缠许久,闹得安阙城人尽皆知。闵恣的母亲江夫人便托人求到长嬴这边,长嬴做主替他们解了这段姻缘。
“殿下这些天在宫里住的多,祖父没找到与殿下说话的机会,得知我今日来公主府,便让我给殿下带句话。”闵恣抬眼一笑,“御林军的冯燎有谋逆之心,其父冯尧光恐怕也不能令人心安,便想召冯老将军与其他三个异姓王一同回安阙城,否则陛下高枕难眠。”
长嬴失笑:“是闵丞相睡不着觉了吧?”
闵恣咦了声,也笑。
闵恣长在佛前,快到出嫁的年纪才被家里接回安阙城,与家中情分不深,因此带话就是带话,绝对没有多嘴的想法。
反倒是对长嬴,闵恣心存感念。
关于闵恣的婚事,其实长嬴也是受人之托。
恰巧这个人今日也递了拜帖。
花厅外,女使引着周止盈走进来,打量了一眼美名在外的周姑娘,提起另一位客人:“闵三小姐也在呢。”
周止盈平时混在各个未建成的木头堆里,穿得很随意,但今日庄重多了,穿的是一身明显是新衣裳的雪色襕衫,温文尔雅。
听了女使的话,周止盈先应了声,解释自己早就知道,过了会儿,她又问道:“闵三气色如何?”
“这倒没瞧真切,”她们走到了门口,女使站定,笑意盈盈道,“姑娘自己瞧瞧吧,请进。”
几年前明州大旱,再加上当时成王蓄意起兵,引起明州州境内叛乱不休。长嬴便是在那时亲赴明州平叛,结识了在明州修水利的周止盈。
君子之交,偶尔来往。
若非那日在狱中闵恣提起,长嬴甚至不知道周止盈与闵恣之间的事。
“我与阿恣是在前几年的一个花宴上认识的。她怪得很,我便多注意了几眼。”
周止盈坐在闵恣旁边,打量着闵恣的气色,发现人虽然变化不大,却显然憔悴许多。闵恣对周止盈笑了笑,示意她安心。
长嬴放下茶杯,凝眸把两人关系看了个透,却不点破,只是从容地移开目光,道:“前些年花匠们大批迁到安阙城,那阵子天天都是赏花宴,确实热闹。这些年倒没那么多了。”
“旁的府上都没新意,也就不爱炫耀了。我看公主府里的花草倒不循旧,”闵恣说,“一看就是用了心。”
“堂春喜欢带着花匠瞎折腾,净种些野花野草。”长嬴的眸中带了笑,“你们常来府上看看花草,也免得堂春寂寞。”
周止盈:“怎么没见燕姑娘?”
长嬴随口说:“还没醒吧,你们改日再来,她还扎了个秋千呢,也不见她玩几回。”
燕堂春其实醒了。
她醒过来时正好徐仪端药进来,燕堂春最怕苦,忙摆手拒绝,却再次发现自己被拷住,手摆不起来。
“好姑娘,给你备了蜜饯,赶紧把药喝了吧。”徐仪苦口婆心地劝导她,“早早让殿下消气放你出去才是要紧事,你愿意在屋里躺上个十天半月的吗?”
燕堂春撇嘴,心道长嬴昨夜也不像是没消气的样子。她不情不愿地用自由的右手接过药,苦着脸一饮而尽,活像喝耗子药。
徐仪连忙见缝插针地往她嘴里丢了块蜜饯,又把托盘里的饴糖放下,对她谆谆教诲:“殿下有什么想法都爱藏在心里,你又不是不知道。乖乖认个错,闹一闹她,她还能真和你置气不成?”
燕堂春嚼着蜜饯,含糊地说:“姐姐帮我做个东西吧。”
徐仪立刻道:“我不敢给你钥匙。”
“我不要这个,”燕堂春撇嘴,“我想拿回我从长嬴这里拿走的那块玉珏。”
听到这个称呼,徐仪若有所思地挑眉。
午后,长嬴出门一趟,回来时给燕堂春带了城西她最爱吃的那家糕点,拎着纸袋进屋时,燕堂春正百无聊赖地倚在床边看书。
“真稀奇,”长嬴把糕点放下,上前去给她打开锁链,说,“你竟然还能想起来看看书。”她随意地把目光往燕堂春手里一扫,看清那书上是什么后,当即就一怔。
燕堂春合上书,眯眼笑:“好看吗?我亲自画的。”
长嬴眨了下眼,下意识收回目光。哗啦几声后,锁链被长嬴扔在地上,长嬴唰得站起身,镇定地说:“兴善堂的藕糖糕,去吃吧。”
燕堂春仰头看着她说:“我想去秋千上吃。”
长嬴:“免谈。”
燕堂春:“什么时候让我出去?”
长嬴:“等残党清干净,等你不会再生事——你还吃不吃了?”
燕氏三代亲王,祖上是跟着太祖皇帝打天下的良将,这个残党恐怕能清个数年,难道长嬴真打算把她关上数年吗?
燕堂春没了胃口,摆摆手说不吃了,长嬴似笑非笑地看着她说:“那你睡会儿?”
燕堂春偏头不乐意地说:“不困。”
“那就把帐子落……”
长嬴还没说完,燕堂春就一跃而起,以最快的速度捂住她的嘴。
燕堂春咬牙说:“我吃,我饿了。你到底怎么才能把我放出去!”
长嬴从善如流地闭上嘴,走到桌子前研墨,假装没听到这个问题。
长嬴倒不是真拘着她,刚开始上锁是因为如今安阙城中还有虎视眈眈的昭王残党。
过了这两天后,基本上也不限制燕堂春在屋里院子里逛,只要不出院子就行。
让燕堂春忍无可忍的只有一点。
那就是不管她干什么,都有四五个女使跟着她。
就连偶尔长嬴不在家,她在噩梦中醒来时,外面都有女使守夜。
有一回燕堂春在院子里憋闷疯了,想甩开人去花园逛逛,结果发现根本甩不开。也不知道徐仪怎么安排的人,跟着的女使一个比一个鬼灵精,根本不吃燕堂春声东击西那一套。
燕堂春数次尝试、屡战屡败,次数多了,她算是明白过来,要么长嬴同意,要么她能打过这些护院,否则她是出不去了。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安阙城迎来了多雨季。
一天傍晚,趁长嬴不在,徐仪悄悄给燕堂春送了样东西。
看着兴奋拿到东西的燕堂春,徐仪犹豫地提醒道:“殿下今日进宫了,不见得能回来。你要不过两天再说呢?”
“她昨夜没和我说,她会回来的。”燕堂春眨眼,“等我好消息。”
长嬴回府时已经深夜,小雨还淅淅沥沥的,草叶被滴滴答答的雨水压弯,水珠坠到地上后,啪嗒一声,草叶一颤,又一次收集新的玉珠。周而复始。
徐仪打着伞把长嬴迎进府门,另一只手提着灯,暖黄的光驱散黑暗。
“堂春姑娘今日睡得早,方才又醒了一次,可能是在等殿下。”
“唔,”长嬴道,“她这几日总做噩梦,是又惊醒了吗?”
徐仪:“殿下进去瞧瞧吧。”
推开门,长嬴一怔。
屋里的光都熄了,只有床头的烛火还亮着,视线被不由自主地引向床边位置。
而红帐垂下,帐内有个高瘦的身影。
长嬴叹了口气,如临大敌地打起精神。
红帐内的燕堂春开了口,声音很轻地说:“表姐,我总是睡不好,梦到母亲,梦到你。”
长嬴避而不答,她走进屋后到屏风后换了身干净衣裳,才想起没关门,又退回去关上门,才到桌边点灯。
长嬴问:“今天做了什么?”
帐子后面的声音轻轻地回答:“读书,今天读了李义山。”
“记住哪句了吗?”
“隔雨红楼,寥落白门。”
正此时,烛火渐渐亮起来,摇曳到火光晃得屋内明暗交错,长嬴半边脸被映得明亮,眼底却晦暗不清。
长嬴忽然有些口渴,走到桌边去倒水。
正此时,床边的燕堂春说:“好亮。”
长嬴肩一颤,似有所察地回过头,见燕堂春从帐子里走了出来。
燕堂春只穿着浅红的中衣,长发披着,连小辫都没编,一双眼睛还是那么亮。
比烛火要亮得多。
窗没关,屋里都是潮气。
水汽从青纱窗处蔓延到桌前,长嬴动了动手指,觉得之间都是湿气,她垂眼看去,才发现是自己手抖洒了水。
燕堂春:“你送给我一块玉,我瞒着你用它做了坏事,抱歉。”
说着,燕堂春走到长嬴面前,手里捧着一个巴掌大小的木盒。
“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1]”燕堂春打开木盒,让它面对着长嬴,她小声说,“我托徐仪姐姐把玉拿回来做成耳珰,和我的心一起还给你。长嬴,你原谅我好不好?”
那木盒里躺着一只孤零零的耳珰,长嬴抬眼看向燕堂春,果不其然见燕堂春的左耳上戴着另一只——
作者有话说:感谢阅读。
[1]李商隐。
小昼天塌了,便看后台边吃饭,吃泡面的时候没注意手碰到手机,不小心给一个读者宝宝点了个举报,我手忙脚乱地再看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这个被我举报的宝宝了。这个对读者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啊啊[爆哭][爆哭]如果有影响的话这个读者应该收到通知,评论区说一声,小昼给你包个大红包道歉哇呜呜呜呜[爆哭][爆哭]对不起ORZ(滑跪
第29章 退步
燕堂春上前一步, 抬手把耳珰为长嬴戴上,然后凑到她脸边亲了一下,小声说:“原谅我。”
耳垂坠着的感觉和脸上温热的触感都让长嬴面上发麻, 她听出燕堂春没说出口的话,无奈叹了口气, 随即慢条斯理地反问道:“然后放你出去?”
燕堂春问:“长嬴, 我们要这样别扭几十年吗?”
几十年是个太漫长的词。
长嬴再次叹气, 终于妥协:“可以出门, 但不能去府外乱跑, 安阙城最近不太平。”
从燕堂春喜出望外的表情来看, 显然是只听了前半句。
但长嬴说的安阙城最近不太平不是假话。
群贤宴办得盛大,不论门第身份召进宫那么多人,这些人全都看到了宫人被毒杀和昭王谋反的全过程。哪怕后面朝廷出面想要压下风声, 文人的笔墨却是压不住的。
他们称赞长嬴射杀昭王的义举, 也批判她不念血缘的冷漠。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文章做了一篇又一篇, 最开始是混乱的, 后来这些人的目的越来越清晰,矛头几乎全部指向一件事——抵制崇嘉长公主入朝听政。
“长公主辅政乃是先帝的遗诏。说句不好听的, 若非长公主力排众议地把陛下从洛阳接回来,当时的大楚连个皇嗣都没有, 轮得到这些人风言风语吗?”
燕堂春听说这件事后, 气得从前院溜达到后院, 直到在门口被拦下来,才又怒气冲冲地往回走,语气很不善地说,“谁背地里说三道四?我去蒙麻袋给他来一顿臭揍!”
女使无奈地跟着她转来转去, 说:“哎呀姑娘,您想想呀,当时在场的人那么多,怎么偏偏就是这几个人出头?群贤宴还是太后全程经手的呢,怎么没人说太后的不是?”
燕堂春长嘶一声,恍然又疑惑:“是有人在引导教唆?会是什么人?”
女使:“您想想谁获利最多呗?”
燕堂春:“谁?”
而获利最多的人很快就浮上了水面。
等到朝廷张贴公文的地方、各个衙门都被沸反盈天的学生堵得水泄不通后,李洛震怒,派禁军捉拿为首学生归案。
原本被非议时,长嬴倒还没怎么在意,这种口舌上取巧的法子虽然好用,却不是多有新意的手段,当初新帝登基时她就用过一次了。这回文章声势虽大,却也到底只是声势罢了。
但为首学生被捉拿入狱后,长嬴暗道不好,瞬间意识到李洛好心办了坏事。
历代文人都有骨头硬的,他们不见得有多么光辉耀眼、青史留名的政绩,其铮铮铁骨却撑着一个又一个朝代的脊梁。对于这些人,可以不加以重用,却绝不能得罪。
而李洛此举却把他们这些人彻底惹炸了锅。
一群学生像入水的油一样沸腾四溅,连有些官员都掺和了进去。
比如宋青。
此时,户部的李勤悄无声息地拜访了一次长嬴,在公主府中留了约莫一个时辰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之后,学生集会越来越多,新上任的禁军首领何超是个明白人,他当然知道学生不能单靠武力镇压,只好日日奔波着苦口婆心地劝那些学生们。
然而他们不买账。
在这样的混乱下,燕堂春算是明白过来什么是“安阙城最近不太平”。
风波越闹越大,终于在此时,大朝会上,李洛在崇嘉长公主的提议下,诚请闵太后垂帘听政,与崇嘉长公主一起作为长者辅佐自己政事。
闵太后自言愚昧,三请三让后才勉强同意。
当天,闹事的学生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平息下来,何超赶紧松了口气,命禁军赶紧把抓起来的人放了。
朝会散后,长嬴在新帝登基后第一次去闵太后所居住的静康宫。
两人一同用过晚膳后,已是晨昏交接时,天边橙红的云朵渐渐漂移在宫墙之外,傍晚微凉的风吹进殿内。
宫人有序地进来点灯,待烛火次第燃起,闵太后挥手示意宫人退下,内室便只剩下了闵太后与长赢二人。
闵太后亲自为长赢斟茶,而后矜持地坐回位置,微微笑着道:“自群贤宴后,哀家许久未见你了。”
“多日未见,太后气色不错,”长嬴把茶杯放了回去,并没有沾唇,“前些天府内女使在靶场玩,偶然射下只鸽子,取下一封书信,倒忘了还给太后。”
闵太后笑意有些挂不住。
长嬴指尖捏着张细长的纸条,略抬起眼皮道:“看来太后已经知道这里面写的内容了。”
“家中信鸽,倒让你见笑了。”闵太后深吸一口气,“你又想做什么?”
长嬴冷冷一哂:“当初闵相提的要求,本宫也兑现了,怎么闹那么大风波?”
“父亲行事谨慎,大约是怕殿下不肯吧。”闵太后闭了闭眼,很快又睁眼,恢复了端庄带笑的样子,双手微微交叠着,“不论如何,长嬴,你放心,我与你绝无敌对之心。”
与谁为敌都不是大事,长嬴站起身,已经没了再留下去的耐心。
“希望太后能记住今日的话,否则下一次射下的便不是一只信鸽了。时辰不早了,太后歇着吧。”
闵太后站起身,目送她离开。
回府后,繁星密布,夜空偶有一声夜莺啼。
长嬴发现燕堂春不在屋里。
她头疼地揉揉眉心,把女使们喊进来,询问她的去向。
原本躲在门后不肯出来的几个女使你推我我搡你,最后推了个女使出来。
女使小心翼翼地抬眼瞄了一下长嬴的脸色,很快被镇得低下头去,为难地说:“堂春姑娘说,殿下不让她出府,她又实在向往自由,只好就睡在离府外最近的地方。于是……于是就抱着铺盖卷去睡门房了。”
长嬴扶额:“就没人拦一拦她?”
女使们支支吾吾地不敢说话,正此时,外头有道声音打破了安静:“殿下自己惯出来的混世魔头,哪能指望这些乖姑娘们去镇压?”
长嬴闻声看去,见徐仪走了进来,笑着说:“我刚去门房那边看了看,有两间房,不耽误原本守门的姑娘歇着。堂春姑娘倒也没想闹腾,我看她精神得很,殿下不必烦心。”
长嬴蹙眉:“连你也和她一起胡闹。她想做什么你不知道?”
“但殿下不是也没招么,”徐仪揶揄道,“由着堂春姑娘闹吧,要么闹到她累了服了,要么闹到殿下心软松口呗。”
长嬴摆摆手:“赶紧把她喊回来,我明日带她出门。”
这是让步了。
徐仪含笑应声,一柱香后,燕堂春抱着铺盖卷从门外往内探头。
长嬴凉凉抬眼扫她一眼,又是一哂。
长嬴认出来,燕堂春抱出去的还是她的铺盖卷。
见长嬴并没有要动火的意思,燕堂春嘿嘿一笑,脚步轻快地小跑到床边,哼着小曲儿开始铺床——铺床的间隙,她还腾出手来给长嬴充满诚意地捧上一杯茶。
大晚上得到一杯浓茶的长嬴气笑了。
燕堂春凑上去碰了一下长嬴的唇。
长嬴:“……”
坏了,鬼头有奇招。
但燕堂春费心大半天,最后却只为了出府逛一逛。长嬴气完,心里又蔓延起阵阵心疼。
她看着燕堂春长大,最了解燕堂春不爱拘束。这些天把她拘在府上,的确快把燕堂春这头野豹逼到极限了。
…………
翌日清晨,燕堂春提前出了屋。
自从得知今天可以出门,燕堂春就欢快得很,昨夜就折腾着睡得晚,今日又起了个大早。
趁着日头还没出来,天还不热,燕堂春照例在早上打完一套拳,围着公主府跑了两圈,然后就跑到花厅去和花匠一起收拾花。
长嬴找到燕堂春时,她已经锄了两片土,移植了六盆花,还给整个花厅的花花草草都浇上水,花匠摇着蒲扇休息。
活动完的燕堂春额间都是一层薄汗,她抬手抹了把汗,脸上却沾上泥土,整个人像从花丛里刚钻出来的。
长嬴无奈地走近她,用帕子把人的脸擦干净了,说:“怎么今天这么勤快?”
燕堂春顺势蹭了蹭长嬴的手,笑眯眯地不说话。
长嬴拍拍人的肩膀:“好了,放下东西回去洗洗,徐仪给你备了热水。收拾好再出门。”
前些天闵恣与周止盈来公主府时,她们曾提起过当年安阙城曾有许多花宴,近年来却少了许多。
也是凑巧,群贤宴后有许多特意来安阙城的人还没来得及离开,周止盈的祖母秦老夫人又逢大寿,周家便以贺寿为名,邀安阙城中众人来家中赏花。
周止盈提起此事时眼带笑意:“祖母心宽体胖,潇洒得很。冬日里生了重病,如今并渐渐好起来,又想念热闹了。父亲便想着借这个机会聚一聚亲朋好友。”
本来长嬴只叫人备了贺礼,但想起来燕堂春也格外爱热闹,便又起意亲自去一趟。
盛夏能开的话没有春日里多,周家便临水设宴,以赏荷为要,水面上浮着的荷叶上托着酒水——细看,这哪是荷叶,分明是做成荷叶模样的托盘,利用了小船的功能,能载着酒水吃食在清澈水中漂浮。
一进周府,燕堂春眼睛就亮了。
“不愧是闻名天下的周工书啊,”燕堂春赞叹道,“府邸不见奢华,却处处巧夺天工。”
出门迎接的周止盈正好听到这句话,笑着迎上前去——
作者有话说:感谢阅读。
抱歉晚了会儿,给大家发红包。
另:8.8不更了,夹子当天23点之后更两章补上。今天我去捋一下大纲[抱拳]
第30章 见势
秦老夫人的寿诞上人满为患, 一是为周家,二是为秦老夫人“书绝”美名;除了这两点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秦老夫人出身博岭秦氏。
大楚开国百年, 朝中鱼龙混杂,为首的有三波势力——坐拥江山俯瞰天下的李氏, 当年陪李氏打天下的四大异姓王, 族谱比李氏还长的三大世家。
到如今, 四大异姓王都不足为虑, 昭王已死, 云王靖王在小小封地苟延残喘, 靖王屈居姜邯麾下,暂时掀不起风波。
而三大世家——博岭秦氏、漅州闵氏、抚安赵氏中,原本以秦氏为首, 赵氏次之, 闵氏垫底。但自从闵氏女入主中宫, 闵道忠闵道恩等人把持朝政后, 秦赵二家便屈居人后。
不过, 秦赵再被排挤,也总归是底蕴身后的世家, 三家不过是差个“势”,其实分不出明显差距来。再者周家虽与秦氏是姻亲, 却始终走的是“纯臣”的路, 与大家关系都不算好——也就都不算坏。朝中人人都是人精, 赴秦老夫人之宴的人自然趋之若鹜。
而秦老夫人是个奇女子,她单名“锦”,号笔上书。秦锦年少成名,书画一绝, 特立独行,直到三十岁都没有成亲。直到寒门出身的周探花崭露头角,游街时与当时楼上看热闹的秦小姐遥遥对视——二人一见钟情,结了姻缘,很快生下独子周静。
但后来秦老夫人因故与家中断绝关系,周家也受世家排挤,从此离开安阙城。直到十五年前周静被先帝特诏进工部,秦锦才又重新回到安阙城。那时的她六十五岁。
周止盈生母早逝,长于周静膝下,与周静一样是个木头疯子,痴迷建筑。经周静与周止盈父女之手的水利庇护的县域有十数之多,前几年青祺宫的修缮就有周氏之功。
而最初举荐周止盈入工部领职、成为大楚第一个外朝女官的人,是长嬴。
周止盈引着长嬴与燕堂春进府,一路上还要应付各种人,显然已经忙得脚不沾地。长嬴便道:“老夫人在席上了吗?”
“尚未,”提起祖母,周止盈眉眼都是无奈的笑,“祖母病久才愈,正好今日热闹,要卯足了劲地装饰自己,这会儿估计还在梳妆呢。”
“本宫带堂春去单独见见老夫人吧。”长嬴道,“你自去忙你的。”
周止盈一怔,而后才想起来秦老夫人曾经教过崇嘉长公主习字,二人有一段不深不浅的师生情分。就连燕堂春也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这份情。
周止盈回过神来,招手喊了个下人过来,对长嬴道:“既如此,殿下请自便。”
由人引路,长嬴与燕堂春一同往后院走去,一路上繁花似锦、燕雀和鸣,花香驱散了暑热。
燕堂春说:“我记得你把秦老夫人的字送给了昭王。”
“前段时间的寿诞?是有这回事,不还是你送的吗。”长嬴偏过头,左耳上戴着的玉质耳珰折射出温润的光泽,“不过在某人大义灭亲之后,王府就被抄了,陛下知道后,那副字如今又回到了公主府的库房里。”
“左手倒右手,”燕堂春啧了声,假装听不懂“某人”是谁,只摇着头说,“也成,否则糟蹋了老夫人的字。”
长嬴笑:“你认多少字?还知道什么是糟蹋?”
这话就纯是调侃了。燕堂春虽然不爱看书,但也跟着长嬴在宫里读过几年书,怎么会不识字——
作者有话说:感谢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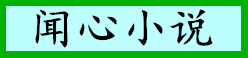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