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风声在窗外呜咽,乐锦不敢点灯,摸索着下床,听见外头声响心里空落落地害怕,像钻进来一只鬼。
金帛的房门被吱嘎一声推开一条小缝,乐锦蹲在门外,一只眼睛往里头观察。
黑漆漆的,没有动静,连呼吸声都很微弱。
手指渐渐伸进门缝,接着是手掌,手腕,手臂……乐锦溜了进来。
金帛有问题。他的面容是假的,故意用了张以假乱真的面具遮盖起来。
白日发现这一点时,乐锦心下轰然一声巨响,整个人天旋地转。
世上对她这样阴魂不散的,只有一个人。
金帛安然睡着,屋子里又没有灯,乐锦要检查他的面孔只能无限靠近他。
蹑手蹑脚趴在金帛枕边,她屏住呼吸,睁大了眼睛一丝不苟观察他的颈部和下颌。但眼睛都快睁裂了却还没有找见那条可疑的粘痕。
可恶的雪夜,今晚出月亮该多好?
乐锦按捺不住急躁,心脏怦怦跳起来。
要不摸一下?看看是否像自己猜测的那样有问题?万一是自己看错了,金帛就是金帛,那也不必提心吊胆。但要是把他摸醒了……
乐锦伸出去的指尖停在半空,在离金帛脖颈一寸处微微发抖。
还是别捅破吧。管他是那个人还是金帛,等她回洛京的时候两人都可以分道扬镳。她装一装若无其事,混过去得了。
乐锦拿定主意,只当今晚她没来过。
正要挪步出去,谁知蹲下去的时候踩到了一点裙子,乐锦整个人不受控制朝右边歪了一下,双臂在空中划了半圈才堪堪稳住。
心脏吓得几乎停滞,片刻之后才放松下来。
一双晶亮的眼睛看着她。
“啊!!!”
乐锦双腿一软,瘫坐在床前。
“怎么要走?不摸摸看吗?”
似乎是乐锦进来时忘记了关门,夜风夹着碎雪吹到了背脊上,浑身温度霎时间没了。
金帛的声音变了。不再低哑粗粝,而是含着柔和的笑意,像冰泉始解那样清明悦耳。
可这悦耳的嗓音却将乐锦的神志击碎了。她坐在地上,双目呆愣看着他。
金帛回望,视线在她脸上停留了很久很久,久到乐锦觉得自己变成了无知无觉的石头。
他眼神里漫出来一种悲凉,嘴角弯起,笑得像哭。
“终于……终于轮到你在夜里端详我了。”
“为什么……”乐锦失神嗫嚅,重复着这三个字。
金帛撑起身子,拉起乐锦一只手去触碰自己脸上的伤疤。乐锦指尖瑟缩,飞速收回手,在自己怀里紧紧攥着。
他哑然失笑,不想勉强乐锦,双手摸去下颌与脖颈相连处,轻轻捻搓,一张薄如蝉翼的面皮被揭了下来。
黝黑的夜里风雪簌簌,乐锦仰头看着一个散发男人撕开了自己的皮,露出平常伪装下那张艳丽风情的脸。
她瞳孔无限缩小,颤动,心头那个惊恐的猜测成真了。她伸出手指哆嗦指着他的脸,嘴唇蠕动却说不出任何一个字。
孟殊台,毁容了。
红褐色的伤疤像蜘蛛一样盘踞在他面颊上,与玉色肌肤冲撞在一起,仿佛一尊摔坏的玉观音露出了冰肌包裹下血红的肉纹。
凉中带腥。
他低头苦笑,“我自作自受。”
一股尖锐的心酸直冲乐锦的鼻尖,两颗泪珠毫无征兆掉落下来。
“你把自己折腾成这样是要做什么?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安生呢?也不肯给我安生……”
她在泣泪,他却在笑。
“不可能了。”
孟殊台曲指刮掉乐锦挂在两腮的泪珠,温柔道:“我恶毒卑劣,残忍疯癫,怎么安生?”
他摇头,含笑的嗓音里满是绝望,“阿锦,就让我生生世世缠绕你吧。”
“我不自渡,我只要你。”
两人所隔咫尺却有天罗地网,一种从五脏六腑之间升出的无力感阴凉地代替了乐锦的血管,伏游全身。
她缓缓抱住双膝,仰头看着他,语气极度平静。
“如果我偏不要你呢?”
孟殊台笑得温良无害,“没关系,你不要我的人,那我就把自己一点点切下来送给你。我不是已经送你一根拇指了吗?”
那只残缺的手在漆黑中张开剩下的手指,孟殊台满怀期待看着它,看着自己的肢体:“我身体的每一处倘若能归于你,那便是安生。”
把自己的身体切下来送给她,那不就是在她面前碎尸?乐锦胃里一阵恶心,当场呕了一下。
孟殊台起身下床,学着乐锦的姿势也坐在地上,肩头靠着她的肩头,很亲昵似的。
“阿锦,你要我吧,好不好?”
他的声音很轻很轻,如同含着气的耳语吹在乐锦耳垂。
“你可以收留救助一个不相干的金帛,为什么不能对我仁慈一点?”
被她捡到,孟殊台一开始很开心。他如愿以偿在她身边留下来了。可是……乐锦对“金帛”太好了。为他请大夫,为他抓药熬药,关心他的身体,甚至会在雪地里紧紧抓住他的臂膀带他回家……
凭什么?!
扭曲得不成样子的醋意在孟殊台心底爆发,他期待着乐锦发现他的伪装,一巴掌扇在“金帛”脸上,让他滚,让他离得越远越好。
可是她明明发现了,却视而不见,甚至故意回避,打算装作相安无事。
所以,是不是只要不是他“孟殊台”,乐锦就会包容偏爱?
凭什么……到底凭什么……
寂静的屋子里,乐锦听见自己鼻子重重的呼气声。
她累了,累得不想和这个疯子理论争执。
“是不是让你在我身边,你就会乖一些?”乐锦麻木转头,一双清澈的眼睛前所未有的冷。
孟殊台被她的目光冰了一下,但仍然点头。
乐锦双眼一闭,侧头吻上孟殊台的双唇。她的鼻尖和嘴唇都凉凉的,落在他脸上像冰雨。
不管了,早死早超生,把这疯子喂饱,大家求个清净。
孟殊台喉结吞咽,承接着这吻,心脏仿佛野火燎原,摧枯拉朽烧下去,焰灰共舞,卷曲翻腾飞向暴雨将倾的天空。
唇舌水声潮湿粘着,他感受到乐锦轻轻缓缓地推拉着,软滑的小舌引诱他去往极乐。
突然,他停了下来。
“你,怎么会?”
乐锦抬眸瞄了孟殊台一眼,勾起唇角笑了笑。
“我成婚了啊。这有什么稀奇?”她故意挑开这个事实,浅浅的眉毛挑衅似的一扬。
孟殊台眼底陡然晦暗,一双眼睛黑沉沉,像一望无际的深海,潜伏着不知名的异兽。
手掌猛得按住乐锦后脑勺,他的吻幕天席地,汹涌夺走她的呼吸。
“唔……”
舌根从疼痛到被吮吸的失去知觉,乐锦心底出现了细微的恐惧,他吻的像是要吞人,不容退让,只有贪婪和饥饿。
一定要把她嚼碎了吞咽进腹才肯罢休。
乐锦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即将晕厥过去,只得用尽力气抓挠孟殊台背部,可惜只是徒劳。
他不肯放,凶狠地像要把她拖进无间地狱里去。
不知过了多久,孟殊台才依依不舍松开乐锦的双唇,喉咙里低低发出一声喟叹。
乐锦脑袋晕晕沉沉靠在孟殊台脖颈,眼皮沉得似有千斤重。
“可以吗?”
他喘着气问,乐锦两眼一闭,揽住他脖颈骂了一句,“不许留印记,你没资格。”
孟殊台吻了下她的发心,算是答应。双臂勾住她的腿弯将人抱在床上。
衣带松开,她的胸口,肩头被轻轻啄吻,细细密密得填满每寸肌肤。
忽然,有点点水珠掉到她皮肤上,烫得乐锦一缩。她强撑着睁开眼,孟殊台的长睫湿润,颤抖如蝶翼。
“阿锦,我爱你。”
他忽然停住了往下的动作,鼻尖贴住乐锦的侧脸,像个委屈的小孩。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她不回应他,他就一遍遍反复嗫嚅,如同虔诚祷告,祈求神迹一现。
她是他的神女,是他无边荒芜中可怜的臆想,高尚的崇拜。
乐锦心里忽然生出一点悲凉。她偏过头,微若无声“嗯”了一下。
那一声声告白终于有了回声。
孟殊台呼吸一顿,接着狂喜,吻遍乐锦的身体,在她的温热中如痴如醉。
一只孤鬼,沾了她的琼脂玉露,生出白骨,有了人形。敲碎骨头,流出的骨髓便是粘稠的欲望。
孟殊台用骨髓浸透乐锦,做了一场淋漓酣梦。
乐锦瘫软在他臂弯,正枕在那烧伤的疤痕上。孟殊台嘴角噙笑轻轻拍哄着她。
乐锦气若游丝,和元芳随在一起时从未这样精疲力尽过。他最爱惜她,哪怕自己没尽兴也会忍嘴;可孟殊台却不,拉着她欢爱如同赴死。
她的发尾被他绕在指尖,一圈一圈打转。
“阿锦,我好还是他好?”
孟殊台贴贴乐锦的额头提醒她别睡,先回答了他这个问题。
乐锦眉头皱了皱,偏头一口咬在孟殊台手臂伤疤上表达自己的不满。
“啊……”他笑,拍了拍乐锦的脸,“别咬别咬,疼,那里还有伤。”
孟殊台低下头去,在乐锦耳旁哑声诱惑:“阿锦,亲亲它吧,亲亲那伤口就不疼了……”
乐锦一条眼缝睨着他,烦躁地用唇贴了贴,敷衍他。
然而只是敷衍,孟殊台也觉心满意足,笑着含住乐锦耳垂轻轻啮咬。
乐锦随他去,眼皮合上就再没睁开。
——
元芳随来接乐锦那日是个晴天。
乐锦把要告诉姜璎云的事一条一条列出来封装好,揣在自己兜里。从屋里走出去时,阳光大的晃眼睛。
元芳随一见她,赶忙从门外跑进来,一把揽她入怀,语调腻歪得一句话拐十个弯。
“好夫人,我想你想得要疯了,你有没有想我?”
乐锦笑靥如花抬手回抱他,手腕上一根旧红绳系着小铃铛,铃铃铃的响。
还没听到回答,元芳随忽然看见屋子里还有个人。
一个五官平常还被烧了一半脸颊的男人自屋里抱着一叠书籍出来,朝着元芳随点头致意。
“这位是……”
乐锦牙齿咬了咬口腔里的软肉,面色尽力平常:“他叫金帛。我看酒厂劳作之人里,不少家中有孩子,就想着给他们找个教书先生。金先生是外乡人,暂时住在我这里。”
乐锦和孟殊台约法三章,今后他便住在清溪镇,好好教导酒厂的孩子们,算是为从前赎罪。乐锦和元芳随之间他不得破坏,若有时间,她会回来看他。
元芳随一脸了然,眉梢轻挑和乐锦悄悄道:“他脸上怎么这么吓人……”
乐锦戳了戳他侧腰,“又不关你的事。”
孟殊台在院子里晒书,倒是真听了乐锦的安排,一副与她清清白白的样子,在元芳随面前并不多看她一眼。
乐锦朝他摆了摆手,“金先生告辞。”
说完便牵着元芳随出了小院子,她没回头,没注意到孟殊台卷起袖子,手腕露出一截和她一样的金铃红绳,朝她也挥了挥。
马车一路往洛京赶,乐锦把怀里的书信掏出来拿给元芳随看,叽叽喳喳讲着这段日子在清溪镇的历练,像只欢喜的雀儿。
元芳随拿着书信却没看,目光只注视着她,宠溺中还带了那么点酸。
“这么高兴啊?我看你都快把我们的出游给忘了……”
“怎么会!”乐锦抱住他胳膊晃晃,甜甜道:“等回洛京把这些交给堂嫂,我们马上就南下,玩到除夕再回来好不好?”
元芳随灿然笑道,“听你的。反正我这辈子都交给你了,你说了算。”
“油嘴滑舌。”
乐锦嘟囔他一句,挑开车帘往外头眺望。
山野俊秀,晴光十里,今天是个好天气。
她心情醺然,快乐地想:虽然两头跑肯定有些麻烦,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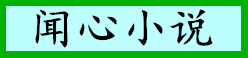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