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正扉不明就里:“做什么?”
“猜个谜。”戎叔晚将唇落在他耳尖上, 而后缓慢下移,落在耳垂上:“方才大人说世上有辣人,我却不信。我想尝尝——大人的谜底是什么?兴许果真是甜的。”
“你……”
“就算大人是辣的, 我也想尝尝。”戎叔晚拿唇轻轻摩挲他的耳垂肉, 怜惜似的玩弄,“若是大人不愿, 就权当我——吃醉了造次。我向大人赔罪, 请大人原谅。”
徐正扉侧脸,将整个脑袋都埋进他胸间, 因喉间干涩而迟迟答不出话来,然而,乱喘的呼吸却暴露了心中所想。
那酒意醉意、那热气仿佛雾水一样,熏得两个人都湿漉漉的, 面颊忍不住发热起来。皮肤上涨起来一层似有若无的颤栗电流,只略听见对方的声息就感觉被刺了一下。
“大人吃醉了, 我也吃醉了。”
“大人?为何不说话,我可以尝尝吗?”
眼见他将话问得越来越直白, 徐正扉羞恼道:“这等氛围,你就非得问明白吗?你就……蠢货。”
戎叔晚将唇挪到他唇边,挨着他的嘴角,热滚着热, 在喉咙和腹腔都烧出激流来,但他却只是发出一个仿佛困惑的低沉音节:“就什么?”
徐正扉被人烫得都颤抖起来,猛然涌上来的情愫复杂、急促;他只好慌乱闭眼,扯挂住这呆货的脖颈,于黑暗上主动吻了上去。
“唔……”
待这样一个不安和激烈的吻结束。徐正扉唇瓣已经肿起来一片,但刚过渡了两口呼吸, 嘴唇便又被封住了。
这次,戎叔晚吻得很慢,很柔。
——仿佛真的是在细致地品尝。
他将人的舌尖勾来缠去,再舔过软腭无数次。他细细的吸吮,技巧丰富的蹂躏,从充满浓重怜惜的亲吻里,交付出去的,更像是一种安抚似的。
良久,那个吻才结束。
徐正扉喘气,已经出了一身细汗。
戎叔晚缓慢去舔他的唇,声息哑得厉害:“大人是甜的。”
“胡说……”
戎叔晚扣住他的手腕摁在头顶,整个人欺身压上去。他只是纯粹的吻在他脖颈软肉上,嗅闻着:“兴许是辣的,不然何以叫我嗓子都哑了。大概是我没品出来——还能再尝尝吗?”
徐正扉轻推他:“今儿,你还想吃个饱吗?”
戎叔晚轻笑起来,仿佛为这话的荒诞而不知所措。
他躺回原处,将人捞进怀里抱紧,坦诚道:“只可惜,大人这样害怕的时候也不多,能轮得到我来伺候的日子,就更不多了……”
徐正扉没吭声。
沉默了不知多久,在无尽暗色里,戎叔晚忽然轻轻叹了口气,朝怀里人发问:“待我赢了那个约定的筹码,大人归我吗?”
“……”
徐正扉没动静,好像是睡着了。
戎叔晚自嘲轻笑了一声,低头吻了吻人头顶:“怨我多心了,竟还肖想这等。”
他知道,没有那天。
比起肖想,他更愿意相信,眼前之人不过是兴起才寻他开心,拿他当个逗趣儿的玩意罢了。
名冠天下的贵公子,终究要用瘦削两肩担起这沉重江山来,与那颗熠熠生辉的北辰星一道,为这政事清明,倾付心力。
他们一颗闪过一颗,而自己,不过是隐没在黯淡角落的一颗雪。直至被冻透了,便坠落在苍茫大地,任人捏踩着脏下去,涂抹成史册刀锋下的墨点。
他缓缓地收紧手臂,折转翻身,又垂眼去看他。但这样紧密地拥抱着,他只能看见徐正扉的头顶……
如此短暂的时刻,他竟然有点同情谢祯。
谢祯拄着刀镇守四海,纵是死身千万次仍不肯退缩。不管是抛声名、洒热血,献上性命、粉身碎骨,还是耍泼打滚,总是要求那位目光垂怜……
虽然叫那位主子为难的厉害,可他却那样勇,笨拙的、义无反顾的爱,再笃定不过。
戎叔晚却不是。
他烂透了的心只爱权力。
他杀人如麻、睚眦必报,却善于审时度势,明白进退。权力之外,他从不肖想不属于他的东西……徐郎如是,真心如是。
那短暂如春风一抹流逝在心底的温存,无法叫他驻足。
得了真心,却须得用更多的东西去换,太麻烦,也实在不划算。他已经搭进去了一条腿,除了贱命一条,再没有更值钱的了。
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他心里明明是这样想的!——
可他仍伸出手去摸徐正扉散落在耳畔的柔软头发。
他莫名想到的,全是这人的好。嘴利,却从不觉得他出身卑贱,而是引他为半个知己。
他想,徐郎待自己,应当有几分真心。
尽管,藏在那双看不透的眼睛下,情志如镜花水月,摇摇晃着难以捕捉……戎叔晚全无把握。
可他知道,徐正扉曾含笑目睹他玩弄那些残忍卑劣的手段,亦钦佩他瘸着腿往上爬的本事——他们默契地不作声。
那条通天梯向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是同类。
作知己,戎叔晚自觉配不上。但是,作同路人,他想,兴许自己还有几分用处。
忽然——
一只手摸上他的眼睛。
黑暗中,那位含着笑开口了:“怎么叹气?何时成了伤春悲秋之人?既作了约定,自然归你。”
戎叔晚被人吓了一跳:“什么?”
“我说,待你赢了那个筹码,我自然归你。”徐正扉倦倦的打了个哈欠,手指往下慢慢地爬,只落在那薄唇上,捻弄着笑:“不要长吁短叹的,吵得人睡不好。”
戎叔晚低头:“……”
——“我不要。”
徐正扉“嗯”了一声,上扬的音调很明显:“什么你不要?”
“大人,我不要。”戎叔晚道:“小的要不起……”
“你这坏胚子。”徐正扉窝在他怀里,侧转身,猛地一个抬腿,顶的人闷哼一声……“说什么不要?”
戎叔晚痛声道:“你……嘶,大人吃醉了。”
徐正扉明白他的意思:“既吃醉了,说话更不需负责了。今日给你说些酒后狂言,扉的心里话,你自听着便是——待明早太阳一照,就跟今夜的雪一样,全不作数了。”
戎叔晚磨牙,“亏得我没信。”
“若是信了如何?”
“信了就要被大人伤透心。”
“你这等心肠,也怕叫人伤?”徐正扉道:“说来也怪,扉这样的大好人,你不敢要,倒是敢往府里招拢些厉害娘子呢。”
“……”
戎叔晚气结:“行,大好人。求大好人放我一马,方才失言,总行了吧。”
徐正扉薅着他的襟领,将人扯近在跟前,低声笑骂道:“你这浪货休要与我装傻,焉以为扉不知道你肚皮里装的什么坏水?既心眼里敢想,就别逃,枉为大丈夫。”
戎叔晚装傻:“没有。”
徐正扉问:“那你要不要?”
戎叔晚反倒哑了火。他着实的不敢要。
徐郎青眼他,倒要受天下人嘲笑了……他算什么?
再若是两人走得近,惹了君主猜忌,与二人都是麻烦。何况,朝中这么多眼目,树敌不少,他们岂可任性妄为?
徐正扉恶狠狠道:“戎先之,你只有一次机会。若说不要,也好,你我先前的约定作废,日后——扉便是你顶顶好的同僚。若说了……”
——“要!”
戎叔晚沉默片刻,又强调:“要,我说要。”
徐正扉哼笑:“若说了要,就更得小心了。若你日后再敢为这等事躲,扉定要连你另外那条腿也砍瘸了不可。”
戎叔晚轻咽了下空气:“大人好厉害的手段,现今后悔,还有余地吗?”
徐正扉在他腰上狠掐了一把。
戎叔晚闷声吃痛,嘶气唤他:“只问一问,又没说后悔。大人怎的半点不饶呢!”
“你这样冷心冷肺的,叫人不踏实。”徐正扉缓缓坐起身来,他扭头看戎叔晚一眼,又抱怨道:“扉最烦你这人。本就害怕,又叫你唉声叹气地吵醒了……现如今,只掐你两下解气,已经算是轻饶你,还敢再说什么后悔不后悔?”
说着,他跪直身子去够窗扇,自朦胧的影绰中打开一条细缝往外看,果然瞧见雪下得更厉害了些,院中已见苍茫白雾。
“仍下着呢。”
戎叔晚自他身后锁住人,却说道:“不悔,我哪里敢后悔?大人这样厉害,我巴不得呢!”
才说完这句,他便靠紧过去,顺手将窗扇阖紧,而后捞住人窄腰,拖进软被里裹了个严实,仿佛又多余乱讲几遍似的:“我要,谁说不要了。”
徐正扉哼笑:“谁问你了?”
戎叔晚捏住他的两腮,将人嘴巴捏的嘟起来,才凑上去狠狠地啄了一口:“大人没问,我自作多情想说,可好?”
“诶,你这厮占我便宜……”
戎叔晚不认,反而笑道:“我最不明白。你们这些文雅之人,怎就那样爱瞧些雪呀花儿呀的?别磨人了,快睡吧……明儿一早,我要进宫。”
“哦?你进宫做什么?”
“晚些时候,听人来禀告,说太后与钟离策有心要宴请你,绝不是好事。”戎叔晚道:“既我答应‘要’了,现如今又不能反悔。可不得明儿一早就去打探打探消息么?免得才到手,没等捂热乎,就又叫人捉走了。”
徐正扉啧声:“好啊你,我不给你这颗定心丸吃,你倒打定了主意见死不救——枉费我这样有心待你。”
戎叔晚笑,又叫人掐了几把。
“疼,轻点儿……”
“活该。”
戎叔晚道:“你早些睡。明儿一早,我回来,给你带城东巷子里新烤的杏仁酥,好不好?”
徐正扉嘟囔着翻身,又被人捞回去了。
“算你识相,这还差不多。”——
作者有话说:徐正扉:杏仁酥我要两包![星星眼]
戎叔晚:买两个卖杏仁酥的老板(捉回家里:现做!!)[让我康康]
杏仁酥老板: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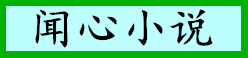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
【请收藏闻心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